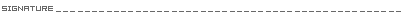四年前在上海求学,于学人书店七五折购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草原帝国》,翻阅中乐趣多多,购书之前就对“上帝之鞭”阿提拉感兴趣,虽然书中只是略微提到一节。后来即在央视电影频道中看到《ATTILA》,一部具有相当娱乐性,有些让人发噱剧情的史诗片。匈奴王阿提拉,孟德斯鸠(Montesquieu)视其为伟大的世界君主之一,认为这个住在木头房子里的人不仅仅是欧洲野蛮民族的领袖,也是欧洲文明民族的领袖;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这位法兰西学院院士,一生潜心研究东方历史与文化,则说他是草原之子。至今在匈牙利和土耳其,阿提拉仍然是男孩子们用的名字,甚至有人自称是阿提拉的后代。而临毕业那年又于学人书店购得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董继平译《阿提拉•尤若夫诗歌》,同批购得的有《曼德尔施塔姆诗选》《聂鲁达诗选》。按说后两者是慕名购得,毕竟早先读过他们的零星篇什,而前者阿提拉•尤若夫则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外,全然陌生,有一种新鲜的意外之喜。便常收集有关他的文字及资料。回福州后,认识吴季,发现他对阿提拉•尤若夫的诗歌亦有偏爱,他觉得董继平译诗语感往往很差,像特拉克尔的诗被他译得几乎没有了味道。但这本《阿提拉•尤若夫诗选》却奇怪地还不错。吴季也曾推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孙用等人合译的《尤若夫诗选》。可能尤若夫诗歌的无产阶级属性与吴季的品性及热衷的事业相关,不久吴季就赴广州参加工人运动联盟工作,在一篇他的笔记中,提到尤若夫的某些诗可以印成传单到大街上散发给民众,这无妨于它们是真正的艺术品。我以为这很是褒奖,能为民众广为传颂的诗篇该是有何等不朽的精神价值。
可能阿提拉这个名字所具备的无上荣光,照耀并彻底沐浴阿蒂拉•尤若夫——一位二十世纪匈牙利最伟大的诗人——身心。那个威慑罗马教皇,策马在莱茵河饮水,车子踏过西欧的“上帝之鞭”,他的死因至今仍然是一个谜。而阿提拉•尤若夫自杀那年所撰写的《履历书》中,坦诚正是童年阅读到阿提拉王的传奇故事,与阿提拉王同名的那种震撼和喜悦强烈冲击了他,甚至成为将他导向文学的引线。他认为他该有伟大的阿提拉王一样的雄心与抱负,如此天真的品性,可能我们年少时也有,但却贯穿了他一生。仿佛只有锦绣文章才能给他带来慰籍,此外便是漫长的冬夜。在贫困孤独中,他敏感、神经质,自杀几乎是他生活中的应然命题。“死亡潜伏在/里面,外面。/像一只受惊的耗子。”(《剧痛》)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首语即提及:“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 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阿提拉•尤若夫生活的时代正如他曾说过的,“这个时代是银行家和将军的时代。”我们可以循着他的文字以及文字中的感情去了解他过去艰苦的生活,艰苦的无产阶级阵营,以及同样艰苦的匈牙利的昨天。根据科学的调查研究,在转型社会里,由于社会动荡和生活压力,各年龄组人口均有显著高于其他社会的同年龄组人口的自杀率和他杀率。无疑,阿提拉•尤若夫所处的二三十年代,这个时段的匈牙利社会正在转变和混乱之中,面临着资本家的压榨和法西斯的危胁。“讨饭?偷窃?都逃不了王法——利润总是资本家的!”(《资本利润之歌》)一个人“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但这个人本身并不觉察。”尤若夫的自杀行为或许与他长期承受的巨大压力和短期内突然爆发的沉重压力有密切关联。这其中存在一个核心:信仰的争执,并由此导致内心的焦虑。阿提拉•尤若夫是一位坚定的政府批评家和“右翼激进分子”。1930年,他参加了“非法”的匈牙利共产党,这个时期他的诗歌取得真正的进步,因为这个进步已不仅限于诗歌的技巧层面,而是他的诗歌自觉赋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属性。他的诗歌真实而写意地呈现匈牙利工人阶级兄弟的苦难。他著名的诗篇也都是战斗的信号:打倒资本主义!权力和面包归于劳动者!(《社会主义者》)。革命诗集《打倒资本主义》出版,被检查官查封。1931年开始心理分析治疗,这使得他开始综合研究西蒙德•弗洛伊德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然而,心理治疗并未给他带来益处。“看,这内在的是痛苦,/之外那些,够了,是讬辞,”这是1934年写的,在保持一段距离审视自身的精神问题。当他提倡联合社会民主人士时——这并不为莫斯科主导的同志接受,遭到了一些共产党领导的警告。一些目光短浅的同志认为他描写工人阶级的无限苦难和被压迫生活的诗,是轻视工人阶级,而且诗人的敏感又加深了这一种误解,1933年尤若夫被斯大林主义者指控为法西斯主义者,驱逐出党。前苏联作家大会于莫斯科举办,尤若夫没有受到邀请,这极大地打击了他。当自己执着的信仰被怀疑甚至否弃,自己出发的立场代表的阵营反过来将自己驱逐出去,1935年尤若夫终于因精神严重崩溃,重新进院治疗。在低谷中他写道:“我的眼睛从头部跳出。如果我变得疯狂,请不要伤害我。只要用你强劲的手抱紧我。”
如果说十九世纪末叶以降,整个人类在精神上就始终末能从一种“世纪末”的普遍绝望的情绪中挣脱出来。那二十世纪初匈牙利动荡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剥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失落,构成阿提拉•尤若夫自杀的宏大背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借希腊神话中日神、酒神之口表达了“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不要失掉了梦的情致和乐趣;就算人生是场悲剧,我们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出悲剧,不要失掉了悲剧的壮丽和快慰”的哲学观。
仿佛跟他的爱人躺在一起,
一个醉汉在铁轨上跟他的酒瓶睡在一起,
舒适地打鼾睡到黎明,知道
夜晚已经远去。
风夹杂着种籽吹进他蓬乱的头发,
把他包裹在雾霭里
因此他没有移动,除了一个
奇异地鼓起的胸膛。
就像一个铁路枢纽,他的拳头的坚硬;
他可以像睡在母亲膝盖上那样睡在那里;
他也许衣衫褴褛——他是个年轻人。
对太阳来说没有空间,天空是灰烬;
只有一个醉汉躺在铁轨上,
而远处传来大地的隆隆声。
(——《铁轨上的醉汉》)
对于深夜买醉的人,人们怎不猜想并同情他的遭遇以及他在成人世界中所留有的天真。酒精让人忘却人世的痛苦忧愁,将人引领到绝对自由的时空中,尼采认为艺术和审美的前提就是醉。醉态中,人的整个情绪系统亢奋异常,使人的时空感发生改变,视野开阔,心灵敏感。凭着醉意,他才能感觉到人生的快乐,仿佛跟他的爱人躺在一起,自己被包裹被容纳到宏大的自然之中。也正是在酒的作用下,他没有移动,而是奇异地鼓起胸膛,在他的内心,不但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重新团结了,而且连孤独绝望的心也重新燃烧起来,从小失去的母爱,以及他渴求的爱情。甚至寒冷的夜、荒芜的风景也都远去,取而代之的有着神奇生命力的种籽,是燃烧的太阳。此外一切都是灰烬。尼采以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思的形象,命名个人解体而同作为世界本体的生命意志合为一体的神秘的陶醉境界。在尼采看来,原始的酒神祭,无节制的滥饮,情绪的宣泄,行为的奔放不羁表现了个体自我毁灭和宇宙本体融合的冲动,这是悲剧艺术的起源。
阿提拉•尤若夫天真地贯彻了这哲学,虽然其自杀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阿提拉•尤若夫犯有信仰失落后严重的抑郁症状;在贫穷面前无能为力的尖锐的长期的生存的压力感;低下的生活质量;以往的自杀企图;以及与一些不理解他诗歌的人的矛盾。可以理解,最后任何一根芦苇都有把骆驼压垮的可能,或者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25年尤若夫出版第二本诗集《不是我呼喊》,他因一首革命诗歌,《以纯洁之心》,而被驱逐离校,该诗遭到得势的教授,安塔尔•胡格尔(Antal Horger)攻击,这人破灭了阿提拉想成为一名教师的愿望。尤若夫在诗中写道:“我无父,无母。得不到上帝也没有故里。没有摇篮,没有尸布。没有吻和爱抚。三天来我没吃过什么,无论丰盛与否。我的二十年即是力量。我的二十年待价而沽。倘若没有人需要它们,魔鬼会来买走。我以纯洁之心发誓:如果需要,杀了谁也不惜。我将被捕获乃至绞杀。葬于神秘大地,滋生死亡的草棵蔓过我异常纯洁的心。”(《以纯洁的心》)。在他的诗歌《冬夜》中,冬夜。/像它体内的一个更小的夜晚/一列货车/到达低沼地/星星在它的烟里盘旋/摇晃着穿过/深不可测的无限而被熄灭。(《冬夜》)可见,尤若夫的诗歌具有一种悲观到了尽头的的不可把握性。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世界之夜——人类生存的虚无的暗夜,在这夜里,“痛苦,死亡,爱的本质都不再是明朗的了”。如此对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普遍怀疑的心态,构成人类自身无法摆脱的梦魇,其中,死亡无疑是个体生命与生具来的漆黑的底色和背景,投射出恒久的巨大阴影。阿提拉•尤若夫仿佛自己笔下疲倦的人,完全被冬夜的阴影笼罩,只求滋生死亡的草棵蔓过异常纯洁的心。那时,“傍晚用长柄勺舀出沉寂。/我是它的一片温暖的面包。/天空正在歇息,群星出来/落在河上,在我的头颅上闪耀。”(《一个疲倦的人》)阿提拉他为自杀展开过描述,因为他有一段不成功的对自杀的尝试。回忆他少时不成功的自杀,他没有对死亡的恐惧,而是深深地陷入自我感动,感动于他的亲人们会怎样悔恨过去对待他的一切不公。而他最后成功的自杀,则是在巴拉顿小镇(Balatonszárszó)卧轨自杀身亡。一个村里的疯子、一个销售代理商、一个火车管理员目击了这场事故。巴拉顿,位于匈牙利湖南面的一个小镇,如今人们喜欢携全家到那里度假,看玄武岩的石柱,尝醇香的葡萄酒,远离喧嚣的闹市欣赏稀有的鸟类和种类繁多的野生植物。而当时在此处,阿提拉•尤若夫失去知觉,不省人事。虽然年仅32岁,但他已承受了够多痛楚,在铁路的平交道他躺下忍受着最后一次痛楚。这是一个老旧的小车站,车票是纸卡,而车站的时刻表示呈现圆筒状。小镇沿路的建筑全为平房,庭院种着清爽花草。感觉淳朴、温馨。仿佛阿提拉的诗歌本身,尽管他的诗歌忧郁,但同样表达了作者对美好和谐生活的信仰。
贫穷是导致他自杀的外在的物质性因素,阿提拉•尤若夫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工人阶级生活区。贫穷让他痛苦,让他写下悲伤,写下巨大的负担压迫着他,写下穷人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为了让我们吃几片面包,/我们的父亲劳动了一生。/无法可施,只得辛苦地劳动着,连上帝都不关心我们”。(《青年进行曲》)事实上,上帝不关心尤若夫,尤若夫的父亲也不关心尤若夫。他的父亲,隆•尤若夫,一个罗马尼亚移民工,肥皂厂工作,在小尤若夫三岁时抛弃了家庭,他原本计划前往美国,最终老死罗马尼亚。于阿提拉而言,他生命最初的关键几年,是和他那可怜的姐姐们、被遗弃的亲生母亲一起度过,他的幼年就开始感受到父爱的缺乏。尤若夫和他的两个姐姐都由他的母亲,一个洗衣妇,波尔巴拉•波策,抚养。饥饿是家里的常客,他能拥有的只是时时对将来生活的担心。而担心不久成为现实,他的母亲于1919年圣诞节死于癌症晚期和过度劳累。依弗洛伊德的“童年经验”说,阿提拉•尤若夫的童年是不幸的,这些不幸的经验可能就是他以后悲惨生活的先验。生活在一个破裂的家庭,疏于教养的孩子作为小猪倌寄养在乡下,晨起赶着站到购买食物的队列中,在影院门前卖饮水,甚至在火车站台收拾捡辍柴火和煤。不生火的屋子,破烂的衣服,有窟窿的鞋:这就是尤若夫•阿蒂拉童年时代的感受。极其贫穷中,母亲,则是他生活的动力和创作的源泉。在他自杀的1937年,尤若夫晤见托马斯•曼,但他不允许公开朗诵他的诗“致托马斯•曼”,诗中他写道:你当然知道这些:诗人从不撒谎。/真相并不够;尽管它会被遮蔽/告诉我们那些能使脑中充满光芒的事实,/因为,少了其中一个,一切都是暗夜。这些使脑中充满光芒的事实是贫困、孤独。但另一方面,阿提拉更多地为人类世界的爱和希望创作,在一首题为《阿提拉•尤若夫》的诗中他写道:“我真切地爱你,/相信我。确有某物为我秉承/它来自我的母亲”。 母亲本身就是阿提拉诗歌创作的关键词。为什么死亡意象在诗中总是与女人或母亲相关?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学观点,一个成年人以后的思想及人格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他过去的生活经历。人的心理问题与他们不好的童年记忆有关。“我的母亲以给别人洗衣服和打扫屋子来养活我和我的两个姊姊。我的母亲给人家做工,从早到我都在别人家里,我没有父母督促,就常常逃学,过着顽童的生活。”甚至在卧铁轨的那刻,他还是极度渴求母爱,因为没有母爱而极度失望酗酒的醉汉,或者说“醉童”?照弗氏的解释,诗人童年经验中的生活印象决定了其后几乎一生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态度。这些童年经验潜匿在无意识中,通过一些转化,转变成对艺术作品有所贡献的情感泉源。又称俄底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s),在精神分析中指以本能冲动力为核心的一种欲望。通俗地讲是指男性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无论到什么年纪,都总是服从和依恋母亲,在心理上还没有断乳。所谓“情结”是指情感上的一种皈依。“就像一个铁路枢纽,他的拳头的坚硬;/他可以像睡在母亲膝盖上那样睡在那里。”(《铁轨上的醉汉》)。而远处,确是传来大地的隆隆声。
我爱你,如同婴儿含啜母亲的乳房,
暗穴隐忍着深不可测,
厅堂由灯光照耀得金碧辉煌,
魂灵热爱焰火,肉体渴望安宁!
我爱你如终要老去的人,
贪恋他们生生不息的时辰!
(——选自《颂歌》)
阿蒂拉•尤若夫的一生,是困厄的一生,也是孤独的的一生。他一生极度贫困并患有神经衰弱症。他同个时代作家亚瑟•库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常居在国外,声称总是梦见母国的人:“异常的孤独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如此的紧张。匈牙利人都有集体的神经衰弱症。”阿提拉•尤若夫当时卧轨才年方三十七,而他的心态甚至比不上终要老去的人。终要老去的人还有对人世的眷恋,贪恋生生不息的时辰,贪恋呼吸,贪恋尘世的光阴。尤若夫心中却是一团寒意,被酒水浸泡的绝望感。那种无父无母,得不到上帝也没有故里;没有摇篮,没有尸布;没有吻和爱抚的绝望和无助。这是他从小既孕育的诗句,在他成年后用文字凝固起来。他能做的就是借助自身与生俱来的瑰丽的想象力,去回忆甚至虚构。惟有回忆给他带来安详,他能在安详的情绪下看见这样伟大的母性,善解人意和令人心疼,得到邻里以及所有劳动人民尊重的劳动着的母亲。这是令人尊敬的光辉的母亲。她慈祥,在生长柔弱而温馨的黄昏的光线中,小坐片刻都是种美的形象。更无用说在劳动中还带着宁静的笑容。这样的母亲是升华到普遍形象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母亲,她们的腿在提着东西时颤抖,她们的头疼痛于熨烫衣服。然而就是这样被劳动压弯了腰认不出年纪的母亲,她也有自己的梦:有干净的围裙,有邮递员对他问好。阿提拉•尤若夫用自己特异的秉赋细腻地写下自己心里母亲的形象,同样干净,干净地让今天的读者动容,哪怕之间已经有几百年的时间跨度。这不朽的精神价值,的确可让民众广为传颂。
而阿提拉•尤若夫的内心里还有一个接近自己,只与自己亲近,生动的可供撒娇的专属妈妈。这个妈妈在尤若夫婴儿嗷嗷待哺时就形成于他脑海。
现在我的挂念磨蹭你身
整整一个礼拜,衣篓里抚养
你的屋子吱嘎有声,你一定爬上楼梯
直去干燥屋顶上的通风口
那时,我生就老实
如何能尖叫、跺脚甚至大声喊:
这浮肿的洗衣房不需要母亲
带走我,去别处过活
但你依旧如此静静地辛劳
没责骂我,连看我一眼也没有
这些吊晒的衣服将会煦暖并飘荡
高扬上空,翻腾着
现在迟了以致再没什么可使我烦心
我的母亲,你是位多么高大的人
漫过天空的你的灰发飘荡
你的蓝色漂白粉都染蓝了上天的水域
(——《妈妈》)
尤若夫作为自己以往生活的亲历者和沉湎过去的回忆者,用独特的体验方式,把自己幼小稚嫩的生命与当时妈妈高大的形象用心地统一在妈妈洗衣的劳动的背景下,一种“返归本心”、诗一般美好的往昔浮现在字里行间。自我的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温情而又无限伤感的场景呈现,本真意识和血性情怀的交融,全通过生动朴素的劳动人民的语言淋漓尽致地表达。困厄的现实压得人喘不过气,诗人沉湎于文字呈现的过去了的有爱世界,甚至把它当作唯一的世界,也就是说,诗人认真而又虔诚地向美好的世界注入大量的真实感情,但当现实与虚幻产生断裂的时候,诗人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极想抛掉生活之重担的愿望,死亡的意念也就应运而生了。“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是一个诗人的世界”,阿提拉•尤若夫真诚地把自己放在诗人的位置上,他最后一年的诗歌,与其说是一首首直面诗人心灵的诗歌,不如说是诗人自己心灵的真实写照,是向死的遗言。
这个铁轨上的醉汉,顽童般用死来抗争现实,渴望找寻母爱,重新体验幼时在母亲身边的撒娇,九岁时他的自杀正是一种撒娇,“当我想象我自己死去并且消失了,她们会怎样热泪盈眶地想起我,我极为感动。”可见尤若夫自幼是多么渴望被爱被关怀。躺在铁轨时,尤若夫年纪仅仅32岁,但他却写下:带走我,去别处过活。“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人只有在极度困顿的时候才要呼喊回到母亲身边。冰冷铁轨上躺着酒瓶和酒瓶的主人。那个夜晚的这个铁路的枢纽直接通向破碎和死亡,并且无限延伸至冬夜里这个衣衫褴褛年轻人渴望低诉与呢喃的母亲那边。一个醉汉躺在铁轨上,他其实是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
这是为什么
陌生人推搡,揍打的孩子
要回到母亲身边。
只有这里你可以真切地笑,真切地哭
魂灵,只有这里你能包容你自身
这是你的家。
(——选自《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