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史·“85美术新潮”之黄专 :走出集体主义的民主幻想 口述史·“85美术新潮”之黄专 :走出集体主义的民主幻想 |
 惘月 惘月

 等级:版主
文章:6663
积分:40119
注册:2003年5月5日
等级:版主
文章:6663
积分:40119
注册:2003年5月5日
|
小 大 楼主 个人展示 | QQ | 邮箱 | 主页 | 发短信 | 加为好友 |
|
ArtWorld:看你的简历知道你在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你的专业和美术领域有一定的距离,怎样一种机缘使你接触到了当代艺术? 黄专: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大学毕业分到山区教书,那几年基本上完全是封闭的。唯一可以交流的是诗人王家新。王家新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上大学的时候是一个很风云的人物分配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和我分到了同一所大学,他后来调到了北京,在《诗刊》杂志社工作。和他的交流使我对现代艺术有了一定的认识。1984年左右我认识了皮道坚老师,这给我提供了接触当代艺术的一个契机。当时我想考研究生,通过皮道坚先生的介绍,我考上了阮璞先生的研究生。 ArtWorld:这样说来,“85美术新潮”这段时间你在武汉,阮璞先生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美术史,你对当代艺术的兴趣是怎么培养起来的? 黄专:“85美术新潮”我只是参与者、旁观者,没有资格评价它。“85”本身不是一种很规范的称呼,“85”的下限是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那么它的上限是什么?其实79年的“星星画会”应该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端,而“85”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延续。 ArtWorld:把“思潮”作为刊名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ArtWorld:《美术思潮》是“85美术新潮”时期的“两刊一报”之一,开始编辑工作的时候是怎样一种思路? 黄专:其实当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目标。我上大学的时候,中国文化就在经历着一种启蒙性的变革,我们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剔除旧的专制文化,至于要建立什么东西?大家都不清楚。具体到当时的美术领域来讲,有“星星画会”这个基础。84年左右各地都有新的思潮,《中国美术报》、《江苏画刊》、《美术思潮》合称为“两刊一报”,其实这些杂志之问没有太多的联系。《中国美术报》比较偏重于“运动”的报道,《江苏画刊》比较平衡一些。《美术思潮》想在理论上有所建设。 ArtWorld:具体到当时的实际工作环境,又是怎样一种一情况?黄专:很辛苦,经费也不多,每一期的编辑费只有30块钱。我们找到一个很小的地方印刷厂,那里印刷费比较便宜。因为我们这个杂志赚不到什么钱,工人都不愿意加班,我们就用自己的钱请他们吃面。老板喜欢艺术为了取得他的支持,给老板挂了一个“责任编辑”的名字。那时候大家有一股热情,想把美术创作从专制过渡到民主,就是很简单的一种想法。 ArtWorld:除你们几人外,参与《美术思潮》编辑的理论家还有那些人? 黄专:有几批人。我和严善錞属于第一批,后来祝斌、李松也调过来了。外地来的人也很多,栗宪庭参与过,邵宏和杨小彦也参与过。彭德有一个优点,他的思想很开放,他经常请外边的编辑来编辑《美术思潮》。可惜的是,1987年这个杂志不得不停掉了,一个原因是因为环境压力,一个原因在于经费,另外在文联内部做这件事情压力很大。要了解湖北美术界的况,有三个人最有发言权,那就是周韶华、皮道坚、彭德、我当时的状态类似你现在,就是帮他们做一些具体工作,就是在这段时期,我的思想也出现了变化。 ArtWorld:能具体讲一下这种变化吗? 黄专:86年前后我有一个转变,这种转变和我们结识范景中有关系。我大学毕业就认识了严善錞,我俩一直保持了一种阅读上的、研究上的合作关系。我记得当时我读的书很乱,康德的书也读,柏格森的书也读:我通过严善錞认识了范景中,他那个时候正在做引进外国美术史研究方法的工作,认识范景中使我认识到一种新的民主思想。 ArtWorld:你说,“范景中使我认识到一种新的民主思想”,也就是说,你在此前,坚持了另一种“民主”思想? 黄专:在此之前,我认为通过引入一种新的文化,冲击旧有文化就可以达到民主,但是我逐渐发现这种想法太简单了,新的文化也可能导致专制。当时中国当代艺术理论界和美术界的一些现象不容乐观,我甚至有些厌倦。 ArtWorld:你见到了什么现象?意识到了什么问题? 黄专:当时的条件下,就当代艺术来讲,已经分成了南北两部分,北方有“北方艺术群体”,比如王广义、舒群、刘彦等一批人。南方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杭州的张培力,他们创建了“池社”。另一部分是厦门的黄永冰。但是无论南方和北方,主体文化还是一种“大文化”、 “理性主义” 、“时代精神”等一些词汇笼罩着中国美术界。 ArtWorld:采访之前我刚好看到你的一篇文章《中国现代美术的两难》。你在这篇文章里面集中阐释了对当时美术界的批评。”我称之为现代美术的形而上学倾向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首先,它认定艺术的本体意义在于它传达的是某种属于人类的永恒超验的文化精神——至于这种精神是绝对的理性力量还是某种来自我们自身的‘生命力’的冲动,抑或是与我们民族‘本土精神’紧密相连的‘灵性’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精神总是由每一个时代中少数走在历史前列的贤哲所代表显现的。美术的病态和衰落正反映了我们民族时代精神力量的衰落,因此,美术的现实使命和崇高目标就是高扬人类的理性精神。这种使命从根本上讲是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而不是艺术的,不能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相反只能妨碍它的实现,所以,我们至少应当避开对艺术的‘纯语言’或‘纯形式’的探究。我想借用波普尔在批判历史决定论时所使用过的两个名词,把上面的表述概括为‘艺术的整体主义’和‘艺术的本质主义’。” 你的整篇文章是用波普尔的哲学理论来阐释你的批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的美术界的理性主义”。 黄专:1989年高名潞把这篇文章发表在了《美术》杂志上,而且发到了很重要的位置上,他在理论上表现出了包容性,因为我所说的一些问题正是他在倡导的。 ArtWorld:这里面蕴含着你所说的新的民主思想? 黄专:波普尔在他的书中讲得很明确那种“整体主义”只能导致历史决定论——人可以决定历史规律,设定历史规律,设定历史目标,这个历史目标是一些先知领导人民来实现,这最终必然导致专制主义。当时的美术界这种现象非常明显。80年代有两种思想潮流,一种是黑格尔式的理性主义,柏格森式的非理性主义;还有另外一种思潮就是解构主义等一类后现代的思潮。我们的主张介于两者之间,针对解构主义,我们强调历史的客观性;针对历史决定论,我们强调“试错”理论,强调历史不可能有它的目标,我们强调历史的“或然性”。我们承认历史是进步的,但是我们不相信历史有先验的历史规律。 ArtWorld:我在采访的时候曾经从三个角度接触到对集权思想的批判,你从理论上反对“本质主义”和“理性主义”,有的艺术家从地域讲对“北京中心”的不适应,有的艺术家直接指出,北京当代艺术的领导人当了领袖以后,也会是非常独裁的! 黄专:这种理论只会导致专制,不会导致民主。他们的结果只能导致“皇朝”更替,而不是民主,不会导致一种新文化形态出现。启蒙时代可以使用两种武器:一种类似于法国的斗争模式,用武力和直接的社会对抗解决问题。还有一种就是利用“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来自于德国哲学。如果没有波普尔的话,或许我也会觉得“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是一种很有用的东西,我也会认为只有“改朝换代”才会有民主。 ArtWorld:可以具体谈一下范景中对你们的影响吗? 黄专:思想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就是范景中。他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人对于名利场的东西他比较厌恶,他也从来不承认他参与过“85美术新潮”其实他的思想通过我们折射到了“85美术思潮”之中。他总是劝我们,对我们说:名利场诱惑太大了,会使我们放弃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有的听了,有的没有听,当然这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从人格上讲,可以使我起敬的人就是范景中。 ArtWorld:80年代后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就是“哲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你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在80年代,艺术成为社会学的工具。你如何看待用“运动”来界定“85”。 黄专:哲学其实也变成了社会学的工具。用“运动”界定“85”本身就是一个很革命的想法,起初这也是我参与当代艺术的一个动因,但是后来我发现,“革命”是不对的。我后来喜欢波普尔所说的渐进式的改革,他反对革命。其实波普尔是揭露专制制度最深刻的一位哲学家,他尽管是位物理学家,但是他的哲学理念完全没有过时,很多西方社会的模式都是按照他的模式建构的。那时候我们的呼声很小,影响不了什么东西,但是从内心来讲,我们强调任何人都不要以掌握历史规律自居。当时我们认为民主社会的敌人就是各种类型的集体主义、本质主义和“革命思想”。波普尔曾经说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所有革命都是要人牺牲的。但是任何理论只要要人牺牲,他就可能是一种坏理论。”其实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很难被人接受的。 ArtWorld:在地域关系上有没有感觉湖北是“地方”而北京是“中央”? 黄专:北京是中心,当时确实有这种感觉对北京的几个大腕确实如雷贯耳。我和他们在价值观上有一致性我也一直关注当时的活动。但是从心态上讲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是“85美术新潮”的一员。到现在为止我还认为栗宪庭是一位很完整的人,他的身上没有很多分裂的东西。他对艺术作品的感觉,他的理论风格我都很欣赏。当时《中国美术报》发表了我和栗宪庭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挺有意思,体现了两种思想的交锋。栗宪庭坚持大文化精神,我提倡分析主义。 ArtWorld:值得注意是你这段时间还一直坚持对中国古代美术史的研究并在1993年出版了《文人画的趣味、图式与价值》一书(黄专、严善錞著1993年12月第1版,上海书画出版社)。 黄专: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两种人文主义,一种是沉思默想的,一种是积极进取的。在我身上这两种东西都在发挥作用。当时我们生硬地运用了“情境逻辑”理论,我们用“情景理论”分析文人画,走出了许多新路,现在看来,研究基础还是比较薄弱。当时潘公凯也比较欣赏我们的研究,鼓励我们做潘天寿的研究。在那种情景下心态比较矛盾:一方面我们想进到历史里面去,学到一些真正的本领;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当时的文化启蒙还是有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作好像是分裂的,但还是有联系的,在精神指向上有关系。总体来讲,和范景中的理论影响有密切关系。有分析能力才可能批判,有了分析能力以后可以自由穿梭于各个领域。80年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思想训练、分析训练的过程。 ArtWorld:80年代你编辑《美术思潮》从理论上接触当代艺术。1989年你参观了“中国现代艺术展”,看到了真正的作品,那是怎样一种感觉? 黄专:这些作品我已经比较熟了,编杂志的时候已经接触到一些,但真正见过的作品不多。我当时感觉最好的是二楼的作品:那些作品比较出色,艺术语言、想法都比较成熟。比如王广义、丁方、耿建翌的作品,徐冰的《天书》、方力钧的素描都在二楼。三楼的感觉就比较弱,全是水墨作品。 ArtWorld:参加那个展览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黄专:通过参观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我认识结交了一些艺术家,和艺术家建立一种关系,这很重要并且那种感情不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上的。我们各地来的人都住在中央美术学院地下室,我记得我与黄永砯、张培力、王广义、舒群等人的见面应该都是在那个时候。那时候只要是搞当代艺术的、就是同志、没有敌人。尽管那是一个草率的时代,但是也有许多实在的东西是有意义的。 ArtWorld:1989年之后王广义到了武汉,和你接触比较多,他的波普转向和你的理论主张有联系吗?采访他的时候,他曾提到他读到了贡布里希的书,看到了“图式修正”这个概念。 黄专:他的转变确实发生在湖北,但是具体影响很难讲。武汉本来就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可以结交很多朋友,彼此之间会相互影响。王广义来到湖北以后和艺术家的交流不是太多和我与严善錞、魏光庆的交往比较多,很谈得来。湖北艺术家是比较注重技术的,他们的波普也是一种很技术的波普,他们当时为什么选择波普?和王广义是一种什么关系?现在大家都避而不谈我想相互之间应该有影响。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政治波普”是对“波普尔主义”的一种“变种”理解。 ArtWorld:“政治波普”艺术家也使用了“历史分析”的方法。 黄专:有些人认为创造一种符号就可以创造一种新的历史,我认为任何历史符号都是具体历史情境的产物,是人为限定的产物,其实没有历史必然性。波普艺术在中国是一个怪胎,它起的作用和在西方所起的作用完全是两回事,在中国,波普艺术变成了一种解构的东西,进行历史批判的东西。 ArtWorld:1992年你参与了“广州双年展”的策划,为什么想到用商业运作的模式来组织一个展览呢? 黄专:90年的时候我就到了广州。当时美术界很消沉,美术活动基本没有,许多美术杂志都消失了。许多艺术家、批评家出国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空间。运动过后我倒是很平静,因为那个运动和我关系不紧密。并且后来我对那场运动开始厌恶。那几年表面看来很平静,其实私下还是有很多活动,比如说王广义当时已经开始画《大批判》系列,他已经开始试着面对商品社会,我也开始接触到一些不同信息。我当时想:可能商业可以使艺术活动合法化。 ArtWorld为什么想到商业呢?和大的社会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黄专:那个展览是吕澎发起的,他来广州找我商量,当时我的想法也在经历一个转变,一种价值上的转变,感觉纯粹用“运动”来推动历史发展是不可能的。80年代接触国外艺术家的作品全是靠画册,连他们属于哪一流派都不知道,更不知道西方艺术世的社会运作模式。后来慢慢了解了一些资讯,通过这些资讯我认识到西方是一个很商业化的社会,有基金会画廊、美术馆等一些机构。为了这个展览造舆论我们还编了一本杂志《艺术市场》,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谁来赞助历史》,现在看来都是些一厢情愿的幻觉。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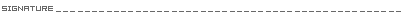 佛缘本是前生定 一笑相逢对故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