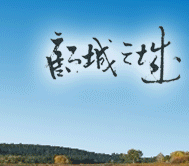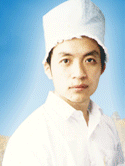[内容摘要]洛夫诗歌中的时间意识表现在对物理时空的超越和解脱,体现着道家、佛家的时间观;并立足于现实时空,而将历史时空对应于现实时空,打破其间的界限,达到物我同一与瞬间的永恒。这与诗人的不羁个性与豪放人格有关,使其在诗歌创作中呈现一种将超越化为永恒的独特意境和神韵。
[关键词]洛夫诗歌;时间意识;超越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_0677(2002)5_0038_04
时间是人类最感困惑,也最富于魅力的话题。时间意识的产生,意味着人们对天地万象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认识和把握,开始脱离了混沌迷茫的状态,逐渐进行秩序性的整理;同时也开始了对于人自身的生老病死、长幼延续的生命过程的焦灼的体验。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由于这是圣人之言,在长期的文化沉积过程中,以江河流逝比喻时间的流逝,并从中体验人事变幻和生命短促,已经成为中国人时或悲悯、时或旷达、时或感伤的潜在思维模式。因此,“时间意识一头连着宇宙意识,另一头连着生命意识。”①当文学作品一旦注入佛禅和老庄思想,就使行文充满机锋,在人与时间相对峙的时候,任自然而获得旷达,由一瞬而转为永恒。
洛夫诗歌中的时间意识,最突出地体现了庄子的和佛家的时间观,达到“物我同一”——时间的超越与“瞬间永恒”——时间的解脱的艺术效果。
首先让我们看一首他创作于1979年的名篇《与李贺共饮》。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在于:以时空的倒错,使千载之前的中唐和现代、古长安和台此遇合,造成古今诗人相晤邀饮的“千古一聚”。借此表达了对古诗人李贺奇情奇才的钦慕之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借此表达一种狂放傲岸的文化人格,对世俗的为人、为文之道的陈腐观念投去不屑的一瞥。“石破/天惊/秋雨吓得骤然凝在半空/这时,我乍见窗外/有客骑驴自长安来/背了一布袋的/骇人的意象/人未至,冰雹般的诗句/已挟冷雨而降”。开篇就起笔不凡,打通了今人与古人的时间隧道。接着诗人邀李贺同饮,“你激情的眼中/温有一壶新酿的花雕/自唐而宋而元而明而清/最后注入/我这小小的酒杯”。从而共诉明主难遇、奇才不获众赏的悲慨。结末时的“相视大笑”,艺术地表达了对诗艺与才情的高度自信,和对古今权贵的轻蔑之情,是一种气质上的深切认同。可以说,不斤斤于功名利禄,不与时俗争高下。而求纵意吟哦,自得于心,是沟通古今二诗人的一种豁达胸襟。
尤其可以称道的是,洛夫笔下的古人,不是在记忆里作为历史中的人物出现的,而是就如熟知的朋友一般,作为同一时空环境下的相平等的人物出现的。也就是说诗人与抒情对象,与往昔今天,与天地万物,达到了想象中的融汇同一。这是一种时空观念上的超越。我们翻开洛夫的诗集《魔歌》,就会在其自序中看到这样一段话:“……诗人首先必须把自身割成碎片,而后揉入一切事物之中,使个人的生命与天地的生命融为一体。作为一个诗人,我必须意识到:太阳的温热也就是我血液的温热,冰雪的寒冷也就是我肌肤的寒冷,我随云絮而遨游八荒,海洋因我的激动而咆哮,我一挥手,群山奔走;我一歌唱,一株果树在风中受孕,叶落花堕,我的肢体也随之碎裂成片;我可以看到‘山鸟通过一幅画而溶入自然本身’,我可以听到树中年轮旋转的声音。”②这段表白,甚至整个《自序》,俨然是一篇新的齐物论,“我与天地并生”,“万物与我同一”的思想淋漓尽致,蕴含其中。“物我同一”、“同一心境”,都意味着时空的无始无终无限无边,也正是所谓的“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太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的道家“时间观”。道家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个顺乎自然继续无间地演化生存的过程,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人不过是宇宙万物中之一体。他应当以物观物,而没有权力也没有必要把自己的观点、概念强行套在万物之上。人只能依靠无知无为否弃外取追逐而返归于内心,启明道心的寂照,从而达到不疲于奔命而洒然自适自在的自由之境,超越一切对峙,升入无我之境,即虚无、超越时间,即时间的消亡。
多次宣称“我的作品的血系纯然是中国”③的洛夫,在他的诗作中,营造物我同一的诗境,表示出超越时空的时间意识。他在《死亡修辞学》中写道:“我的头壳炸裂在树中/即结成石榴/在海中/即结成盐/唯有血的方式未变/在最红的时候/洒落”,由“头壳”→“石榴”→“海”→“盐”的系列转换中,没有变的是“血的方式”(即“真我”)。诗人的这颗心就是万物之心,所谓“真我”就是把自身化为一切存在的我。于是由于我们对这个世界完全开放,我们也完全不受这个世界的限制,既没有空间概念,也没有时间意识,是超越时间的存在。“主要乃在/你把歌唱/视为大地的诠释/石头因而赫然发声/河川/沿你的脉管畅行/激流中,诗句坚如卵石/真实的事物在形式中隐没/你用雕刀/说出万物的位置”(《诗人之墓志铭》)。化宏观的宇宙入微观的内心,用生命的灵魂摒弃时间的栅栏,透过内心的体验取消一切外在的形式,主要是“时间的形式”,来探知穷游八荒的真谛。
在《裸奔》中,诗人“多么希望有一只彩堞”(兴许是庄子的蝶)“从呕吐中,扑翅而出”,诗人洒然地把“帽子”、“衣裳”、“鞋子”、“枕头”、“雨伞”、“床铺”、“书籍”、“照片”、“信件”、“诗稿”、“酒壶0”、“手脚”、“骨骼”、“血水”、“眼睛”以及“欢欣”、“愠怒”、“悲痛”、“抑郁”、“仇恨”、“茫然”、这些物质的生理的精神的心理的一切一切摒弃之后,他开始“溶入街衢”、“混入灰尘”、“化入风雪”、“步入树木”、“揉入花香”,遂而升华为“可长可短可刚可柔/或云或雾亦隐亦显/似有似无抑虚抑实/之赤裸”。全诗归结到“溶入”、“混入”、“化入”、“揉入”、“步入”、升华为“赤裸”。也就是“通过消失逃避了存在,又通过存在逃避了存在。”④(着重号为引者加,下同)这就是说运动的东西,它的存在具有瞬间那种无法把握的模棱两可性。因为它刚刚出现就已经是被超越的而且已经外在于我,存在是瞬间的是虚幻的,不存在是虚无的真实的。这听起来似乎玄之又玄,然而这种超越,这种外在于我,这种虚无,根本的内涵就是否定一切以求主体的自由,否定时间的存在以求主体的永恒。《裸奔》之类诗,“裸”且“奔”,“奔”且“裸”,也正是如此。
在洛夫的诗中,不仅在这种抒情类诗中有时空的超越的时间意识,而且抒写自然景物的诗中也如此。常常是,当人们遇到一如受压迫似的一种自然景色时,多少会产生一种纯粹感应。这种感应与其他的感应不同,是与整个宇宙相结合,即以一种与普通全然不相同的方式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关系完整的体系,一个充实的世界。比如《微云》一诗中的微云,虽然有飘逸的空灵,可高高在上的东西,总有一种原性般的压迫力,而诗人洛夫歌唱“微云”:“不羁,不朽,/永恒的存在,真实的虚幻,/无所生长,何以幻灭?”在这种“物我两忘”、“天人相通”的艺术世界里,诗人“就这样,我把自己焚烧”奔向那灿烂而又辉煌的世界,从而“冉冉升起,我们同赴太阳的盛宴”。在超然的内省中,由绚烂趋于宁静,由宁静走向超越,走向时间的超越,而时间也在这“宁静”的“超越”中消亡。总之,洛夫的诗中的“虚无”,是一种“无我无物而又有我有物的艺术世界”,是“物我同一”的契合,是超越了时间,在审美主体中时间意识的消亡。
佛的时间观,是洛夫诗歌中时间意识的第二个突出的特征。佛家主“妙悟”、“妙觉”,强调万法皆空,企图从主观精神上悟得空无的真谛,达到超现实的彼岸。在艺术世界中追求心静、境静、神空、物空,过去——现在——未来,汇合在这一瞬间,生万有的空与化万物的无在这一瞬间,从而达到瞬间永恒,而时间也在这刹那的永恒,摆脱固有的轨道,在审美主体的意识中停滞。“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说,永恒不是空无所有,不是时间的徒然否定,而是时间的全部的、未分割的整体。在整体中,所有时间的因素并不是被撕得粉碎,而是被亲密地揉合起来,于是就有这么一种情况:过去的爱,在一个永在的回溯所形成的永不消失的真实中,重新开花,而现在的生命也就挟有未来希望的和踵事的幼芽了。”⑤这种“永不消失的真实”就意味着意识的焦点在“现在”这一瞬间的状态中运行,而且在运行中扩大了“现在”这个时间点,在刹那间洞见整体和全部的意识,解脱于时间轨道的束缚,使现实世界中时间运行的过去、现在、未来,在这里的艺术观照中以“现在”的当下停止了运行,不再有“过去的时间”,也不再有“未来的时间”,有的是就是“现在”,就是现在的瞬间永恒⑥。
在洛夫的诗歌世界中,充盈着上述时间意识的诗句比比皆是。“筑一切坟墓于耳间,只想听清楚/你们出征时的靴声。”(《石室之死亡·49》)“蓦然回首/远处站着一个望坟而笑的婴儿。”(《石室之死亡·36》)《石室之死亡》是洛夫较有代表性的长诗,主要体现诗人对生与死的体验、感悟和认知。诗中“坟墓”(死者)与“出征时的靴声”(生前),通过诗中的主体(我)运用意象的压缩把这种具有流动性的时间凝结了,停滞了,在这种时间意识作用下,审美主体才能够听坟墓中“你们出征时的靴声”;而“远处”、“望坟”时间化了的空间中,尸骸与婴儿、死亡与生存、冷酷与微笑,都在化动态为静态之中,寓永恒于瞬间。因而凡生凡死、凡死凡生,瞬间之中生也即死!死也即生,生死勿辨,生死难辨。这里与其说是诗人的哲思,还不如说是诗人在禅宗时间观念的支配下,“万古长空,我形而上地潜伏”,“一朝风月,我形而下地骚动”,瞬间永恒,时间解脱束缚而停滞。“左边的鞋印才下午/右边的鞋印已黄昏”(《烟之外》)“回首,乍见昨日秋千架上/冷白如雪的童年/迎面逼来”(《雪地秋千》)。前者把现实中瞬间即可完成的动作,故意在审美中拉长,使瞬间永恒;后者则把已经久远的过去,通过“昨日”这个刚刚过去的较近的时间,一下子拉到眼前,淡化或者是消去之间的跨度,也使时间永恒。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妙在时间意识的解脱而停滞,从而使前者沉闷的心情更沉重,使后者怀念的情感更深厚更亲近。
在《醉汉》中,诗人“把短短的巷子/走成一条/曲折/回荡的/万里愁肠/左一脚/十年/左一脚/十年”,仍然运用时间的“物理瞬间化”反映在“心理上的大延缓”,从而省略那些不能够也不必要的过程,增加了诗歌表达的含蕴。令读者在反复的回味中,体会到思乡的缠绵和持久,体现了诗人诗歌中佛的时间观。而“至于寺钟/传到耳中时已是千年后的余响了”(《寻》),“一仰成秋/再仰冬已深了”(《独饮十五行》),“我抚摩过的手/翻过来/一九二八年的那滴血/仍在掌心沸腾”(《啸》)。这些诗句中,“寺钟”之响,“千年”乃听;两仰之间,由秋到冬;遥远的那滴血,至今沸腾。诸如此类,无不是通过瞬间的审美中的妙悟,来达到永恒的感受。其根本的表达方式是时间的停滞,目的求得梦幻般的瞬间的永恒的同时,使诗人和读者更大程度地领会诗的主旨。
洛夫前此对现代主义“超时空”艺术把握方式的体认,与中国人文传统中“天地与我为一”、“我与天地同在”的观念融通起来,从而使超现实主义泛化为一种广义的东方化的审美方式,这同样是一种时空的超越。从《无的河》经过《魔歌》到《酿酒的石头》,诗人青年时代执著的“挖掘生命、表现生命、诠释生命”的强烈的现代意识,越来越为另一种曾经沧海的中年意识所洗涮,而变得淡然!怆然和超然。在情致上融入彻悟的禅的意蕴和意趣。诗作常将现代的技巧化入古代的意境,或取古代的题材予以现代的诠释和处理。前者如《金龙禅寺》、《随雨声入山而不见雨》等。后者最突出的莫如《长恨歌》。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在一个紧追一个意象暗示中交代出来。情欲迷恋酿成的历史不幸和历史阴影下造成的爱情悲剧,交融在诗中一幕幕极富讽喻效果的戏剧情景之中,使这一悲剧互为矛盾地蕴着人性的和历史的双重意义。传统与现代的两种价值取向,透过人物、事件、情境、意蕴,乃至语言和技巧的强烈对比,赋予这首长诗以很大的艺术张力。这样一来,可以明显看出,洛夫诗歌创作中的时间意识,既有思想者凭藉无限时空,化思想为智慧,为生命的内在体验;也有诗人凭借时间,领略生命的诗情与存在的真谛"品味千百年中国诗人们的洋洋宏卷和涓涓诗语,我们可以读出,时间感受,乃是中国诗人艺术思维中一支敏感而精细的触角,深深植入生命的底蕴,映现着诗人的心灵境界,形成了绵亘不断贯穿古今诗歌中的时间喟叹。这些时间意识,或凝聚着儒家的无奈,或飘逸着道家的轻灵,或萦绕着禅家的空无,形成了独特的传统的民族精神。洛夫的一系列有关时间意识的诗作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只有在思想的无限超越中,才可能达到时间上的永恒。
注释:
①杨义《中国叙事学》《杨义文存》(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20页;
②洛夫《魔歌·自序》,同上169页;
③洛夫《超现实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同上170页;
④萨特《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版288页;
⑤弗利德里希·希勒格尔《文学史讲演》《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327页。
⑥冯前成《心灵锁钥——佛教心理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09—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