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冈山散记】
【黄冈山散记】
眼睛的健康需要广开眼界,只要我们能看得远,我们就永不感到疲倦。
——爱默生
1\高与低
黄冈山,乃东南第一峰,号称华东屋脊,其势不谓不高。然觅遍山顶,不见大树,不见森林,只数棵矮树立于草甸。数丛小竹,卧于其中,刚及膝盖。高山之巅只长矮草竹木,这是大自然高与低的永恒对话,也是哲学高与低的永恒对话。黄冈山之高要求低而成其高。而在山腰的林木中穿行,发现粗大的林木丛中也只偶尔生长几棵低矮的草和树,呈现少有的空旷。大树利用自己宽大的伞盖占领了天空中的阳光和雨露,又利用自己粗大的根须吸尽了地下的养料和水份。矮小的植物生长极为艰难。高阻碍压抑了低的生长,高成其为高往往牺牲了低作代价。
对于黄冈山之高,我是低矮的小草;对于山中的大木,仍是躬身其下的植物。而我在攀援,从低处向高处。没有绝对意义的低与高,低与高是可以改变的。黄冈山之高其实应该在人心里。心里的高度,是值得人一辈子攀登的。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我登黄冈山而小东南,我气势虽比孔子弱些。然而我这双不断问讯生活的脚却并不寂寞。站在山顶,我就比黄冈山高,在高与低之间只有攀登来得最为及时,从生活的低处,获得一种海拔的高度。
站在黄冈山顶,矮小的草木是高大的。草木的低同样借助了伟大的山而成其高。矮小的植物同样有它的海拔。在精神的畏途里在高的压抑和阻碍下。攀登以有路和无路的方式穿行丛林和断崖之间,汗水和血水浇铸着生命的延伸。伟大在召唤,在绝顶之上在云天之上,把我的一生吸引。
人类在寻求伟大而崇高的东西。我不知疲倦地漫步在山谷和峰峦之间。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永远是低矮的小草,做着自己纯然的梦。成长和壮大,衰老和死亡,我无法预测未来。然而我用瞬间的辉煌来昭示生活。
黄冈山,2157、7米的海拔,对于我是2157、7精神的海拔。今天我站在黄冈山上头顶天空,思绪在高与低之间飞翔。中国有海拔五千年的高度有博大精深的古老文化之光。每个人都应该成其为伟人!有民族的自信,不以为自己低人一等,不以为自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蚂蚁。自强不息,把手伸出来托举天空!
我永远匍匐着。我是一个最卑微的人,最底层的劳动者。在通往未来的路上,我质问过谁。当峭壁如生铁一样冰冷而残忍地横着,低变为高是凄迷的,有八万条路径——树木选择了一块沃土不断向天空逼近,而我选择了一双居无定所的脚!
谁在高处窥视着我们。在黄冈山顶,我其实攀登得很累了。我躺在一片美丽的草甸上睡着了,我梦见了自己和黄冈山一样高大,头发变成了草木,有另一个我躺在发丛中。我来自生活的低处,我登上黄冈山主峰,我是很高了,我有了博大的胸襟和宏阔的气势。
2\山中的美
“蛰居林深处,山高更少攀。”坐在木屋的阁楼上独对青山,欣赏苏俊老先生的诗句。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是退的哲学。退隐作为古代知识分子最津津乐道和最崇敬的时尚,它永远闪烁着人类某种隐密的智慧。苏俊老先生坐在这里,吟诗写字,山中之雾时常擦过他的眼睛,或者是星星点点的雾珠误以为他的胡须是草,挂在上面如细小的珍珠。木屋之外是篱笆圈起来的几棵
(1)
梨树,梨果青青压弯了的树枝,不小心就伸到了篱笆之外。篱笆的旁边,巨大的鹅卵石们铺成
的平地,已染上了绿茵茵的青苔。沿石路走数百步就是一清见底又昼夜发出訇声的溪流,溪流傍壁而上的是竹木的黛青和新绿。苏老先生的木屋在两山夹峙之间。他蛰居这里多年。他不是
退隐,因为这里是他的家。我非常羡慕苏老先生能够在黄冈山下拥有这样的木屋和数十年的居住。尽管山高更少攀,我想八十高龄的苏俊老先生,过去肯定多次登过黄冈山。“壮丽黄冈顶,嵯峨众山冠,身临心境阔,目极楚天宽,举足跨闽赣,低头看峰峦,登高知何处,已在白云端。”又“昂然屹立众山巍,独傲东南势壮威。红日时从眼下起,白云常在竹边飞,晴天忽变阴天雨,六月须穿十月衣,若上一层高百尺,可将双手摘星归。”(《黄冈抒怀》)写家乡壮美的诗不下千首,可见老先生对黄冈山山水的衷情。山中的美系住了他的一生。和我聊天的空隙,他靠在门口的竹椅上抽纸烟,目光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这一山一水一木一石一桥。
经过几天的观察,我也发现了黄冈山的美。
在山脚,竹木繁茂,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词“绿韵”来解释四周的主色调。大自然是最优秀的画师,它调好的色增一分大多减一分太少,真是鬼斧胜过人工。毛竹一层层晕染而上,逼近山顶的岩石。它染绿了你的眼睛和你的肺部。自然奔放的笔触,没有理论的枯燥缰硬和陈腐,没有口号的喧嚣和烦杂,像风一样自由地涌过来涌过去。把白色的颜料喷成遐想的雾状,几许朦胧几许神秘。把几棵黛色的冷杉耸立雾中如临空独立的墨点。还有黑色的岩石,黑色的石路和路通向黑色的木屋,像千百年来时间的沉淀物:凝滞而厚重。但它又让水割断和撕裂成一个远方不知名的冲动。木桥是黑色的,水是白色的。衣服是黑色的,少女的手是白皙的。石水缸边,木杵是黑色的,少女的脸是白皙的。在黑白之间流淌着古老的歌谣。而在其它缤纷的色彩之间,晕染着大自然最纯真最舒爽的笑容。
在黄冈山顶,嫩绿的草甸起伏着。墨线勾勒着几棵矮小的松。从山脚直奔山顶,黛色的林木像草原放牧的奔马。风牵动着林涛声正涌向湛蓝的天空和白色的云朵。几点彩色的颜料,野花般窃笑着喘着粗气的我们。几颗黑色的石头也患恐高症一般瘫在了那里。风很蓝,阳光很赤。九月的黄花像散落的碎金,可惜现在是初夏,杜鹃花正在悬崖边脚踏云雾似梦似幻地诱惑着你。还有天上的鸟是自由的白色或黑色。
黄冈山的美,也是听觉的美。
丛林深处,鸟鸣清脆。深谷之中水声訇然如黄钟大吕,而泉水如少女抚琴叮叮咚咚。阵阵风涛卷起松树、栲树、黄连木、冷杉等的衣裙。没有欢乐这就是欢乐,掌声响起,如交响乐潮来回激荡,摄人心魄。阳光穿过树隙,像一锭锭银子打在石头和枯叶上。还有一行六人的脚像敲在大地上行行复行行的问号。我曾在一飞瀑边坐下来歇息,静听瀑声。在瀑布边我看到前人的脚印:几个木工在这里搭建起木屋,他们在其中锯制木料,刨花和木屑溅落的声音和瀑布交缠在一起。更远,我看到一个头裹白巾身穿长衫的古人,反剪着手站在那里,悠长的吟哦声,已被飞瀑声淹盖。一边是生活中的人一边是梦想中的诗。两种声音在交汇。就像我带来尘世的噪声,今天坐在飞瀑之下,要接受怎样的感召和撞击。石头和石头挤在一起,水从中愤怒地冲过。水只有到了深潭才平净下来,但又酝酿着冲向更远的深潭。一点一滴的水打在石头上,众多的水汇合了这巨大的声响。诗人孙桂贞说白岩石一样砸下来,李白说银河落九天,我说最硬的肺砸在石头上。观瀑实际上是听瀑,在尘世污染了的人得以息心静虑,变得坦坦荡荡,有私变为无私。
黄冈山还有触觉味觉嗅觉的美。踏着枯叶的柔软和苔藓的潮湿,摸着竹木的坚挺和岩石的锐利蛙蛙鱼的滑腻。闻着花草的清香,品着野果的酸甜、泉水的甘冽。我们来到了黄冈山,收获了黄冈山。大自然真是一份色香味俱全的佳肴。蛰居在这样的地方,真让人乐不思蜀。
(2)
3\平步
小路登黄冈山。见有一石壁甚平,朋友问应刻何字。答曰“平步”。
何谓平步?一曰平步青云。如走平路一样一下子爬得很高了,说这个人发达的很快。我说的平步不是平步青云,而是在丛林陡壁上走路,胜似闲庭信步。这是一条小径。向导在前面用刀开路,我们上腾下跳,时而有枯树横在面前,时而有崖壁悬于脚下。过水渠时,脚有点抖。
脚下是万丈深渊,不敢向下看。——大部份路显得平坦异常。在我的想象中,黄冈山之高之陡,攀登的路应该十分奇险。问题是路被茂林遮蔽着,树木使我们深处险径而不自知。这点和我们的生活极为相似,人生是遮蔽着的存在。一整天如履平地不知周遭环境的险恶。
山路在林荫中前行,凉爽之极。踩在柔软的落叶和苔藓上,透过树隙看湛蓝的天空和云朵,我们乐观而悠然,从不计较腐叶中的毒菇,树枝上青蛇的窥伺。刚才有一条焦尾青还在水边吐着蛇信,现在竟有人跳下水抓螃蟹玩呢!尽管跌跤,摔掉眼镜;尽管迷了路,我们仍在崖壁中穿行,踏腐木而过,任凭危险埋在脚下或伏在头顶,因为我们有把困难踏在脚下的勇气。人活着,就应该保持平步的状态,山太高大了,人就显得缈小;世道太艰难了,生活就变得胆怯。人一出生,痛苦就潜伏在那里;死亡就潜伏在那里,随时把你抛向深渊;敌人潜伏在那里,枪潜伏在那里:有形或无形的枪,人啊活得太累了,何不到林中休息,安步当车,或者散步白云深处,飘逸、放纵、自由、高迈。
把遮蔽敞开。紧紧抱住自我的精神,在险径中高视阔步。有这种心境,我们登黄冈山一点也不累。
4\时间之外
自铅山黄岗山镇到桐木关,据说是武夷山大裂谷。桐木江在峡谷奔流着,带着白色的石头。时间莽莽苍苍,不知从何处来,不知到何处去,负荷着历史如一座座沉重的山。
山是破碎的时间,也是凝固的时间。
黄冈山陈列着几具时间的尸体。在黄冈山绝顶,有许多破旧的房子杂陈着。风刮过来刮过去,并没有风化。破砖破窗,废弃的铁罐。东一截西一截的锈铁管。在黄冈山美丽的草甸之中像腐烂的狼骨,有一点阴森和冷。这是林彪时期的军事基地。据当过兵的朋友估计,这里能住一个营的兵力。林彪摔死在蒙古沙漠后,基地没有告竣人就撤走了,留下这横七竖八的遗憾。在西坑也有一栋文革时的建筑,被火烧了,几堵断墙立在那里,墙壁上还留有薰黑的领袖语录,这也是时间的残骸。松涛把我们的目光举得很高,竹林又把我的视线引向开阔。我们在大峡谷徜徉。友把一双筷子和一支铅笔放在衬衣口袋里,他时而拿出笔时而拿出筷子——笔想留下艺术,筷子想饱餐秀色——它们的共性是为了掠取大自然的美,而让时间留存。
我在黑色的木屋前停了下来,吹开岁月的风尘。黑色的窗框,被风抚过九遍被雾亲过九遍。檐雨滴落,阶石被滴出无数个细小的孔,雨打在石孔上激溅出无数个水泡。门两边挂着泛白的对联。对联是苏俊老先生写的。苏公想和时间对抗的笔墨已经脱落。像一个伏在门前哭泣的老妇人。木屋立在石上,巨大的石头肩并肩地扛着人类繁衍生息。屋主人从何而来,在这里住了多少年并不知道。从苏老一家来看,也只往了一百多年,一百多年是极短的瞬间,但老屋毕竟刻下了时间的足迹。从墨黑的瓦上,从腐烂的柱子边,从老人的皱纹里——更应该说从山民的血管中。由于下雨,我们在一栋木屋里歇了下来。山民递来凳子。天泠,山民又端出火盆。友说穿衬衣烤火真有趣。这是山民的真诚和热烈。我想起数天前在苏公家被殷勤接待,酒过三巡茶过五味,带我们上黄冈山------临别,我们走得很远了,八十多岁高龄的苏老先生还站在冷雨
(3)
中向我们挥手,他的儿子竟把我们送到十里开外才止步。山里人的质朴真诚打动了我。是啊,在这里,时间转化为山民性格中的美被永恒保留了下来。
有了人才有桥,我的目光又投掷到桥上。小桥流水人家,这种古老的意境里,我多次走进木桥。经历时间的大冲毁,桥依然在河流之上横着,在木板和木板之间传递着力量,经历了喧哗和和嚣闹,心始终保持着平静。夜晚,月悬于桥间,啊,这天空的信使,只有你夜夜祈扮有一座桥横贯大地,让世间的隔阂,能够沟通,让阻断的爱情能够团圞------木桥上走来一个少女,她欢蹦乱跳,像一个符号留在画中。木桥啊,你是“人”的延伸,你又能承载多少时间呢?如今有人
从我脊背上踏过,我是否能够承载起他们的重量!
在黄冈山,我看到许多林木老死在那里,它虽然避免了刀削斧劈,自然地死亡。但我也看到许多优秀的树木,在刀斧中死去。一切生命都是短暂的,我看不出这两种死有什么不同。树木选择固定的土地营造直达天空的途径,人选择了漫游来完善自我的品性,把时间固定在手里,人是缈小的。在黄冈山山间,水在激射。我们只不过是大自然若有若无的一个点,文明也只不过是人类在大地上留下的一点痕迹。
生命啊,我怎样理解时间和和生存呢?黄冈山大裂谷有一条河作为主动脉,奔腾而下。它把泥沙含在口中,让卵石闲置,让蛮荒和文明陈列两岸。奔流必须有旁观者,任何时代的喧哗和骚乱必须有旁观者。黄冈山独立东南,以时间的态势,耸立在那里,他目睹过世间的一切。而今天我登山,完成了时间的攀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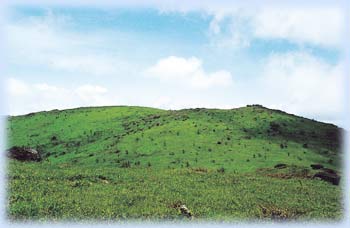

 网站首页→流放地论坛→散文与随笔→ 【黄冈山散记】
网站首页→流放地论坛→散文与随笔→ 【黄冈山散记】


 网站首页→流放地论坛→散文与随笔→ 【黄冈山散记】
网站首页→流放地论坛→散文与随笔→ 【黄冈山散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