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容的《革命军》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
和
苏报案
大陆
金冲及、胡绳武
编者按:本文摘录于金冲及和胡绳武先生的《辛亥革命史稿》。该文真实地记述了中国共和革命之所以爆发的思想原因和历史由来。是一篇信史。但由于文中存在着马列思想的太多浸染,诸如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说教,和指中国的辛亥共和革命是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等等,虽为作者的不得已,但本刊在发表时,还是予以了必要的删节。敬请作者原谅。
正当留日学生中的拒俄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革命思潮在国内也迅速高涨起来。这个高涨的起点,是刚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邹容所写的《革命军》一书在上海的出版。
邹容,原名绍陶,字威丹,四川巴县人,他的父亲邹子璠是个商人。容幼年时,就很有反叛性。十二岁时,第一次参加考试,就因同考官顶撞而退出试场。他对父亲说过:“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戊戌变法时,容年十三,随日本人学和文。“容因此得识诸学门径,习闻欧理绪余,乃浏览种种新籍时报,每有所刺激,好发奇辟可骇之论,又纵谈时事,人因是以谣言局副办呼之。无少长贵贱,如其人腐败,或议有不合,容必面斥之。”一九零一年夏,他到成都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他回家时,给大哥蕴丹写信,痛斥科举制度:“近国家掇难,而必欲糜费千百万之国帑,以与百千万帖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中,而拣其一二尤者,于天下国家,何所裨益?”并劝他大哥:“其从事于崇实致用之学,以裨于人心食道也可。”当他准备留日时,他的舅父刘华廷阻挠他说“中国之弱,乃是天运。”“汝一人岂能挽回?”“若裕为国,试看谭嗣同将头切去,波及父母,好否自知。”邹容在离家到日本后,给他父母去信时,断然表示:“人人俱畏死,则杀身成仁无可言。”只要正义所在,“虽粉身碎骨不计,乃人之义务也。”
 一九二零年春,邹容到达日本东京,进入同文书院学习.“容在蜀时,既有所感触,及东来,日受外界刺激,胸怀愤懑,愈难默弭”,思想更趋激进。凡留学生集会时,他常争先演说,言词犀利悲壮。那时,驻日南洋学生监督姚文甫是清朝政府的忠实走狗,经常排斥和迫害留日爱国学生。马君武不能入成城学校,刘成禺不能入联队,都是他出的主意,“人言籍籍”,“多归怒于姚”。一九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邹容和张继、翁浩、王孝缜、陈由已五人,乘姚文甫有奸私事,排闼直入,持剪刀剪断了他的辫发。把姚辫悬挂留学生会馆,并在旁写到:“南洋学生监督、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四月间,他因此被迫回国。回到上海后,住在爱国学社,和章太炎同寓。与章太炎、章行严、张继十分投合,结为兄弟。这时,正值拒俄运动开始高涨。四月二十七日,他参加了爱国学社在张园召开的拒俄大会。会后,冯镜如等发起组织中国四民总会。四月三十日,四民总会集会,各界一千二百多人参加。蔡元培、马君武等在会上发表演说。会议决定改名国民总会,“以保全国国土国权为目的”,邹容签名入会。接着,他又发起成立中国学生同盟会。国民公会成立不久,内部就发生了分化。康有为的门徒龙泽厚和发起人之一的冯镜如,把它改名国民议政会,计划以七月九日为陈请西太后归政光绪的日子。邹容十分愤怒,带头痛骂冯镜如,爱国学社学生纷纷脱会,国民议政会无形解散。《革命军》这部著作,从邹容自序中的说法来看,大体是在日本时写成的。一九零三年五月,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上海出版的《苏报》在六月九日刊登了章行严的《介绍革命军》和署名“爱读《革命军》者”的《读革命军》,六月十日又刊登了章太炎的《革命军序》。 一九二零年春,邹容到达日本东京,进入同文书院学习.“容在蜀时,既有所感触,及东来,日受外界刺激,胸怀愤懑,愈难默弭”,思想更趋激进。凡留学生集会时,他常争先演说,言词犀利悲壮。那时,驻日南洋学生监督姚文甫是清朝政府的忠实走狗,经常排斥和迫害留日爱国学生。马君武不能入成城学校,刘成禺不能入联队,都是他出的主意,“人言籍籍”,“多归怒于姚”。一九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邹容和张继、翁浩、王孝缜、陈由已五人,乘姚文甫有奸私事,排闼直入,持剪刀剪断了他的辫发。把姚辫悬挂留学生会馆,并在旁写到:“南洋学生监督、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四月间,他因此被迫回国。回到上海后,住在爱国学社,和章太炎同寓。与章太炎、章行严、张继十分投合,结为兄弟。这时,正值拒俄运动开始高涨。四月二十七日,他参加了爱国学社在张园召开的拒俄大会。会后,冯镜如等发起组织中国四民总会。四月三十日,四民总会集会,各界一千二百多人参加。蔡元培、马君武等在会上发表演说。会议决定改名国民总会,“以保全国国土国权为目的”,邹容签名入会。接着,他又发起成立中国学生同盟会。国民公会成立不久,内部就发生了分化。康有为的门徒龙泽厚和发起人之一的冯镜如,把它改名国民议政会,计划以七月九日为陈请西太后归政光绪的日子。邹容十分愤怒,带头痛骂冯镜如,爱国学社学生纷纷脱会,国民议政会无形解散。《革命军》这部著作,从邹容自序中的说法来看,大体是在日本时写成的。一九零三年五月,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上海出版的《苏报》在六月九日刊登了章行严的《介绍革命军》和署名“爱读《革命军》者”的《读革命军》,六月十日又刊登了章太炎的《革命军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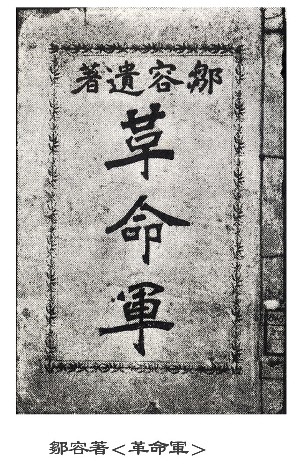 《革命军》这部著作,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占着十分突出的地位。这不仅由于它以通俗晓畅、痛快淋漓的笔墨宣传革命思想,易于为群众所接受,从而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传民主思想、共和革命和号召创建人民共和国的著作。 《革命军》这部著作,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占着十分突出的地位。这不仅由于它以通俗晓畅、痛快淋漓的笔墨宣传革命思想,易于为群众所接受,从而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传民主思想、共和革命和号召创建人民共和国的著作。
一打开《革命军》这本书,劈头就可以读到邹容热情洋溢的对革命的赞颂:
“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魂、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我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我们不妨作一些比较:在邹容之前,孙中山自然是有明确的共和革命思想的,他所领导的革命武装起义的实际活动,也已经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但他自己到这时为止,一直还没有写出比较系统的宣传革命思想的著作,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日报》又因短于学理,不为人所重;一九零一年的《国民报》是有革命倾向的,但它这种倾向常常以隐晦曲折的方式来表达,没有正面地响亮地喊出革命的口号;《江苏》杂志上《革命其可免乎》等文章的发表,已在《革命军》出版以后。象这样旗帜鲜明地高举起革命的旗帜,痛快淋漓,毫不吞吞吐吐地鼓吹革命主张的著作,《革命军》应该算是第一部。它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确实有着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意义,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邹容在《革命军》中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他响亮地喊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他写到:“夫人之爱其种也,必其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世界人种之公理,抑以人种发展历史之一大原因也。”
 他把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集中到“反满”这一点上来,并从三个方面鼓动人们“反满”的情绪:第一,引证《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所载的历史事实,提出“父兄之仇不报,而犹厚颜以事仇人”,“曾祖若有灵,必当不名目于九泉”,来重新激起人们“为父兄报仇”的旧仇。第二,从现实生活中,列举少数满人专有行政官之半额、八旗驻防各省以防汉人、八旗子弟有自然俸禄等事实,来说明满汉两族待遇的不平等,以激发人们的“不平”。第三,从清政府的对外态度中,以上谕中的“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等语来揭露他们卖国媚外的面目,以燃起人们的新恨。从而,要求人们“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推翻清朝政府,“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恢复汉族的国家。 他把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集中到“反满”这一点上来,并从三个方面鼓动人们“反满”的情绪:第一,引证《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所载的历史事实,提出“父兄之仇不报,而犹厚颜以事仇人”,“曾祖若有灵,必当不名目于九泉”,来重新激起人们“为父兄报仇”的旧仇。第二,从现实生活中,列举少数满人专有行政官之半额、八旗驻防各省以防汉人、八旗子弟有自然俸禄等事实,来说明满汉两族待遇的不平等,以激发人们的“不平”。第三,从清政府的对外态度中,以上谕中的“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等语来揭露他们卖国媚外的面目,以燃起人们的新恨。从而,要求人们“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推翻清朝政府,“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恢复汉族的国家。
邹容提出的革命的内容,不只是民族主义这一个方面。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比过去其它人更加鲜明地、系统地宣传了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他从国民的天赋权利这一观点出发来提出问题。写到:“今试问侪何为而革命?必有障碍吾国民天赋权利之恶魔焉,吾侪得而扫除之,以复我天赋之权利。”“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所谓臣也。”“后世之人,不知此义,一任无数之民贼独夫,大盗巨寇,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他还说:“自世界文明日开,而专制政体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故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
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如:“定名中华共和国”;“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这自然是比较彻底的民主共和思想了。
邹容在全书最后,响亮地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象这样旗帜鲜明地宣传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象这样系统地提出实行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邹容也是第一人。
在邹容心目中,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是革命的最高榜样。在他所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中明确地规定:“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他特别推重法国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
《约论》。在他看来,法国革命也好,美国独立也好,都是卢梭等人的学说结出的丰硕果实。他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地写到:
“夫卢梭等学说,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则吾请执卢梭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之土。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伦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木。”
“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得斯鸠《万法精理》、
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邹容《革命军》一书的发表,在当时思想界,有如响起了一声震撼大地的春雷。还由于这本书充满着炽烈的革命热情,笔调又通俗明快、犀利有力,使人读着它就象触到了电流一样,无法平静下来,这就更增强了它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书出版后不久,章行严在六月九日的《苏报》上发表了《读革命军》一文。指出:“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挦櫡往事,积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李商隐于韩碑‘愿书万本诵万遍’,吾于此书也云。”它出版后,翻印流传极广,风行海内外。香港翻印的称《革命先锋》,新加坡翻印的称《图存篇》,上海翻印的,有的称《救世真言》,在横滨与章太炎《驳康有为书》并列,称为《章邹合刊》,还有将它与《扬州十日记》合刊的,销售总数当逾一百万册以上,在清末革命书刊的销数中居第一位。
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曾说:“……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更有赴日留学生感慨地说道:“……我们在去日本的途中,就已经呼吸到了革命的空气;到日本以后,又受到了更多的革命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参加了拒俄学生运动;这样,改良主义思想在我头脑中就逐渐丧失了地位……甚至在思想上便完全和改良主义决裂了。”
 如果说,邹容的《革命军》是从正面阐述了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那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则是从批判改良主义反动理论的论战中,论述了革命的巨大意义。这篇文章,是革命派对改良派正面进行批判中,第一篇思想性和战斗性都比较强的文章;也是在当时产生了巨大革命影响的一篇文章。 如果说,邹容的《革命军》是从正面阐述了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那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则是从批判改良主义反动理论的论战中,论述了革命的巨大意义。这篇文章,是革命派对改良派正面进行批判中,第一篇思想性和战斗性都比较强的文章;也是在当时产生了巨大革命影响的一篇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改良派散布了一系列的谬论,来反对革命,阻挠人们走上革命道路。这些谬论中许多又同社会上长期存留下来的旧传统观念结合在一起,保持着巨大的影响。不坚决批判改良派的谬论,革命高潮的到来是不可能的。对此,章太炎逐一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批驳,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这就帮助许多人从改良派的精神枷锁下解脱出来,很有些所向披靡的气概。
改良派企图用革命将招致流血牺牲,来吓唬人们不要参加革命。章太炎却从历史上论证:在专制政体下,人民要取得政治上的权利,流血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血流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也。”
改良派以人民智力道德低下、不配革命为借口,来反对革命。章太炎则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论证:正是革命实践,才是提高人民觉悟的最有效的途径。
“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且勿举华拿二圣,而举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无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业。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不可已,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事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
改良派以革命会引起社会紊乱为借口,来反对革命。章太炎则指出:革命不只是破坏,同时也是建设:“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改良派将光绪皇帝说成尧舜以来未有的“圣明之主”,要人们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章太炎则竭力揭破这种伪造的神话,打倒这尊虚设的偶像。过去,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的名字俨然神圣不可侵犯,天下臣民是万万说不得的。谁胆敢提一下,就要大祸临头,脑袋就要搬家。章太炎偏偏选准这个目标,直斥光绪的名字。一声“载湉小丑”,震动远近。顽固派为此暴跳如雷,中间派为之目瞪口呆,而革命派却为之扬眉吐气。它在当时所起的那种震动人心的思想解放作用,今天我们已不容易完全体会到了。
对康有为,章太炎更作了尖锐的揭露,指出他那封信名义上写给南北美洲诸华商“要改良不要革命的信”,其实是写给清朝政府看的:“宣布是书,其志岂果在保皇立宪耶?亦使满人闻之,而曰长素(即康有为)固忠贞不贰、竭力致死,以保我满洲者,而向之所传,借遵皇权保中国不保大清诸语,是皆人之所以诬长素者,而非长素固有是言也。荣禄既死,那拉亦髦,载湉春秋方壮,他日复辟,必有其期。而满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势力权籍,或不如荣禄诸奸。则工部主事,可以起复,虽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觊觎矣。”这确是一针见血之论。
 自章太炎《驳康有为书》发表后,传布内外,改良派在爱国群众中的影响大大消弱。这篇作品,在革命派同改良派的理论斗争中,不愧是一篇起了巨大影响的光辉作品。 自章太炎《驳康有为书》发表后,传布内外,改良派在爱国群众中的影响大大消弱。这篇作品,在革命派同改良派的理论斗争中,不愧是一篇起了巨大影响的光辉作品。
但是,《革命军》也好,《驳康有为书》也好,最初还只是秘密的出版物,传布和影响的范围不能不因之受到很大的限制。当章行严为邹容《革命军》题签时,“容曰:‘此秘密小册子,力终捍格难达。革命非公开昌言不为功,将何处得有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供吾徒恣意挥发为哉?’言下唏嘘不置。”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他们的积极活动,《苏报》终于成了他们公开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阵地。
《苏报》,本在一八九六年创刊于上海公共租界内。创办人是胡璋(铁梅),但由其妻日人生驹出面向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主笔最初是邹弢。报纸内容多载市井琐事和作奸犯科的社会新闻,文字粗陋猥亵,曾因刊登黄色新闻并有欺诈勒索等事被人控告。一八九八年,《苏报》为陈范(梦坡)购得。陈原为江西铅县知县,因教案落职,愤而办报,力倡变法。以后,他的女儿陈撷芬又主办《女学报》。一九零二年冬,南洋公学学生退学风潮发生后,东南各校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苏报》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增入‘学界风潮’一门,乃大为阅者之所注目矣。”
爱国学社成立后,由于“仓猝成立,经费不足,因与《苏报》约,每日由学社教员七人轮流担任撰述论说一篇,而《苏报》馆则月赠爱国学社百金。于是,互受其利,而《苏报》遂为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之园地”。一九零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苏报》正式聘请爱国学社章行严为主笔。六月一日,是日苏报大改良,于发论精当时议绝要之处,夹用二样字体,错落出之。是日之论说为《康有为》,其中“‘革命之宣告,殆已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数语,即政府所指控者也。”六月六日,“是日之论说为《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以风闻北京大学堂学生接应东京义勇队者二人被拘,且讹传正法矣。其实并无此事,不过大学堂学生曾上书管学,请力阻俄约耳。而海上风谣四起,一日数惊。故《苏报》有是论。大约此簦议论,乃《苏报》中之最激烈者矣。”七日、八日,《苏报》连续刊载论说《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九日起又连续刊载文章公开向读者介绍邹容的《革命军》,发表大量鼓吹革命的文章。就在这时,《中外日报》发表了《革命驳议》一文,《苏报》在十二日和十三日又连载了章太炎、柳亚子、蔡治民、邹容四人合写的《驳革命驳议》。言词激烈,一切在所不顾。它犹如狂飙卷地袭来,上海新闻界原来沉寂的空气顿时被一扫而空。
这个时期的《苏报》,公然地、毫无顾忌地昌言革命。《康有为》一文中,除指出“革命之宣告殆已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外,还写到:“而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躺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一文用欧洲共和革命时期学生们起来“杀皇帝”、“倒政府”的历史先例,来鼓舞人们大胆地行动起来,写到:“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而京都之学生为中央革命之原动力,是世界所供认者也。巴黎之学生、维也纳之学生、柏林之学生、圣彼得堡之学生,撞自由钟矣,树独立旗矣,杀皇帝矣,倒政府矣。”“北京学生诸君将追其迹,而照耀于二十世纪之历史乎?将为先人雪耻,而壮大吾汉人之声色乎?吾歌之,吾诵之,吾全国之学生将欢迎诸君矣。望诸君自重,诸君胆壮,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吓而敛其动,莫惜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国人之希望。则学生之全体幸甚,中国幸甚。”“中国万岁!中央革命万岁!”
其中,写得更激烈的,是《杀人主义》一文。这篇论说中,虽然表现了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它所表现的那种同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势不两立、鼓吹革命一往无前的精神,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写到:“此仇敌也,以五百万幺魔小丑,盘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税,杀戮我祖宗,殄灭我同胞,蹂躏我文化,束缚我自由。既丁末运,沐猴而冠,己不能守,又复将我兄弟亲戚之身家、性命、财产,双手奉献于碧眼紫髯下。奴颜向外,鬼脸向内。呜呼!借花献佛,一身媚骨是天成;斩草除根,四海人心应不死!今日杀人主义,即复仇主义也,公等其念之。”他还写到:“读法兰西革命史,见夫杀气腾天,悲声匝地,霜寒月白,鸡犬夜惊。悬想当日独夫民贼之末路,英雄志士之手段,未尝不豪兴勃发,不可复遏!黄旗已招展矣。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
 《苏报》对改良派散布的教育救国论、变法维新论等阻挠革命的种种谬论,一一进行了批驳。对教育救国论,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奴隶主义者,以其知识技能尽奴隶之职。国民主义者,以其知识技能尽国民之职。夫以奴隶主义之人,而增其知识,练其技能,则适足以保守其奴隶之范围,完全其奴隶之伎俩,将使奴隶根性永不可拔。是其非教育界之罪人、而我国民之公敌哉!居今日我国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导之脱奴隶就国民。脱奴隶就国民如何?曰:革命!”对变法维新论,他们嘲笑道:“夫大小变法,不过欺饰观听,而无救于中国之亡。”“总之,国民与政府,立于对峙之地者也。革命之权,革命操之,欲革命则竞革命。维新之权,非国民操之,不操之权,而强聒于政府,亦终难躐此革命之一大阶级也。悲夫,放弃国民之天职,而率其四万万神明之同胞,以仰一异种胡儿之鼻息,是又昌言维新者所挟以自豪乎?无量头颅无量血,既造成我新中国前途之资料。畏闻革命者,请先饮汝以一卮血酒,以壮君之胆,毋再饶舌,徒乱乃公意。”这些对改良派的批判,比留日学生刊物如《国民报》等,显得更旗帜鲜明、痛快淋漓,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思想水平。 《苏报》对改良派散布的教育救国论、变法维新论等阻挠革命的种种谬论,一一进行了批驳。对教育救国论,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奴隶主义者,以其知识技能尽奴隶之职。国民主义者,以其知识技能尽国民之职。夫以奴隶主义之人,而增其知识,练其技能,则适足以保守其奴隶之范围,完全其奴隶之伎俩,将使奴隶根性永不可拔。是其非教育界之罪人、而我国民之公敌哉!居今日我国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导之脱奴隶就国民。脱奴隶就国民如何?曰:革命!”对变法维新论,他们嘲笑道:“夫大小变法,不过欺饰观听,而无救于中国之亡。”“总之,国民与政府,立于对峙之地者也。革命之权,革命操之,欲革命则竞革命。维新之权,非国民操之,不操之权,而强聒于政府,亦终难躐此革命之一大阶级也。悲夫,放弃国民之天职,而率其四万万神明之同胞,以仰一异种胡儿之鼻息,是又昌言维新者所挟以自豪乎?无量头颅无量血,既造成我新中国前途之资料。畏闻革命者,请先饮汝以一卮血酒,以壮君之胆,毋再饶舌,徒乱乃公意。”这些对改良派的批判,比留日学生刊物如《国民报》等,显得更旗帜鲜明、痛快淋漓,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思想水平。
《苏报》的不少论说发表以后,外地报刊如香港《中国日报》、厦门《鹭江报》等纷纷选录转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
上海地区的革命宣传活动如此大张旗鼓地迅速展开,自然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极大震动。这年的五、六月间,清朝商吕海寰就函告江苏巡抚恩寿说:“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恩寿就饬上海道袁树勋向各国领事照会,指名要逮捕蔡元培、章太炎、陈范等人。介绍《革命军》的文章在《苏报》上发表后,恩寿再次饬袁树勋,称奉清廷谕旨,要求上海的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工部局,会同查封《苏报》,逮捕章、邹、陈等人。又派候补道俞明震到上海,会同袁树勋办理此事。
六月二十九日,工部局派中西警探到《苏报》馆,捕去报社帐房程吉甫。第二天,到爱国学社逮捕章太炎。章太炎在被捕时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同天,又在《女学报》馆捕去《苏报》办事员钱宝仁和陈范的儿子陈仲开。另有龙泽厚,也因自力军旧案而被指捕,于当晚自动投案。邹容最初由张继藏在虹口一个教士家中,后亦于七月一日到租界巡捕房自动投案。
章太炎被捕后,在狱中致书《新闻报》记者,称:“今日狱事起于满洲政府,以满洲政府与四万万人构此大讼,江督关道则满洲政府之代表,吾辈数人则汉种四万万人之代表。”这封信在七月六日的《苏报》上刊出。第二日,《苏报》就被封闭。
七月十五日,英租界会审公廨组织额外公堂进行审讯。清朝政府委托律师古柏提出控诉,指责《苏报》“挑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云云。章太炎在受审讯时,慷慨陈词,继续宣传革命,说:“因见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满人,故我作书驳之。所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这次诉讼,引起国内舆论的沸腾,成为全国视线集注的焦点。案中的陈中开、钱宝仁、程吉甫三人,因无关重要,被关押四个月后即被释放。章太炎、邹容二人,清朝政府原来坚持要求引渡到南京,准备置于死地。但在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下,拖延到第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租界当局最后只能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可是,邹容在监禁期满前两个多月,竟“因病”死于狱中。“邹容病急时,已许某时某日出狱矣。先一夕服医生药,遂死。故外间生疑,多谓遇毒。”章太炎被关押至一九零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方才出狱。
《苏报》案的发生,对国内思想界的震动是十分巨大的。这件事在上海发生。它对内地所起的打开风气的作用,自然是日本和香港等地所难比拟的。章行严在回忆中说:
“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言词之间,略无忌讳,斥载湉为小丑,比亲贵于贼徒者,维香港东京之刊物能为之,在内地则不敢,抑亦不肯。洵入上者,词锋朝发,缇骑夕至,行见朋徒骇散,机关捣毁,所期者必不达,而目前动乱之局亦难于收摄也。此其机缄启闭,当时明智之士固熟思而审处之。然若言论长此奄奄无生气,将见人心无从振发,凡一运动之所谓高潮无从企及。于是少数激烈奋迅者流,审时度势,谋定后动,往往不惜以身家性命与其所得发踪指示之传达机构,并为爆炸性之一击,期于挽狂澜而东之,合心力于一响,从而收得风起云涌之效。《苏报》案之所由出现,正此物此志也。”
愚蠢的清朝政府,本以为借《苏报》案就可以将当时方兴未艾的革命思潮扑灭下去。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大出反动统治者的意料之外。《苏报》案发生后,在国内知识界引起了更大的激动,更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布。《苏报》第四期的本省时评说得很清楚:
“前日之《苏报》与《革命军》,议论虽激,然而阅此报与此书者几何人也?一般之国民固未尝知其所号呼者为何事,其鼓吹者为何事。今日《苏报》之被禁,章、邹之被锢,其势固已激荡于天下。然‘《苏报》何以被禁,章、邹何以被锢’之一问题,出诸于一般国民者必多,则必应之曰:为逐满故。何为而逐满?则又必应之曰:为汉族受满族之荼毒已不胜其苦,满族实汉族之世仇敌。以此而互相问答,互相传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于是,排满之主义,遂深入于四万万国民之脑髓中。”
他们还特地发表《祝苏报馆之封禁》的时评说:“此后,吾但祝满政府多封报馆;则国民之自由心愈发达,吾中国前途愈光明。吾乃于《苏报》馆之事,飨宴以贺之,燃开花炮以祝之。”另一篇时评中更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后之革命风潮,当为奔涛怒浪,不可遏止。吾不知官吏政府,又将以何术济其穷?”
《苏报》案尚未结束,在北京又发生了清朝政府杖毙参加自立军的沉荩事件。沈荩,原名克诚,字愚溪,湖南长沙人。先时,与谭嗣同、唐才常友善。他在维新派中是思想比较激进的一个,曾说:“新吾湖南,非有一番之破坏,不为功也。”戊戌变法失败后,曾东渡日本。后回上海,参与唐才常主持的自立军事件,为右军统领。但,“荩所恃之主义,乃唯一之破坏主义,不喜学问,无复杂之头脑,故一闻才常之言,以为天下事大可为也。”事败后,潜入北京,秘密居住两年,被人告发。一九零三年五月十九日,被清政府逮捕。这时正在《苏报》案事件起后二十天。沉荩被捕后,被判死刑。这时,正值西太后生辰,嫌在这时行刑会“破其庆典”,于是就下令在狱中杖毙。七月三十一日,清吏用竹鞭捶击沉荩,连续四小时,血肉横飞,乃未绝命,最后用绳子勒毙。
这个事件,充分暴露了清朝政府的野蛮残暴,激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怒。《江苏》杂志的国内时评写道:“夫沈荩以何罪死,满政府固未尝有一纸死罪宣判书以告我国民也。夫杀而不能言其罪,则四万万人孰非可杀之人乎?”,“呜呼!吾向者犹以为满政府不过用其呼尔蹴尔之术以待我汉族,而不知今后竟至于磨刀霍霍而来也。今日杖杀一沉荩,不过小试其新硎之利器耳。血肉横飞,哀呼宛转于槌杖之下,又满政府待我汉族之方法,而我同胞前途之写影也,吾同胞其将何以待之?”章行严更于同年化名“黄中黄”写了《沉荩》的小册子(章太炎在狱中为这本书作了序),书中指出:
“自荩死后,而满政府之丑状尽形呈露,大激动国民之脑筋,发议于各新闻杂志,以为今日可以无故而杀一沉荩,则明日即可以无故尽杀吾四万万同胞。前言满族之虐待我汉族,而尚有忠奴为之解脱,自今观之为何故?同胞视此,则直以为满政府与吾国民宣战之端,吾国民当更有一番严酷之法对待满政府。几致全国之舆论为之一转。”
上海的激进份子又在愚园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到会的有数百人。会上,宣读章太炎所撰的哀词,鞠躬致敬,并有人演说沉荩惨死的事实和今后对待清政府应有的态度。到会的人中间,不少人为之流泪。
这样,从《苏报》案以后,革命思潮在国内,也如决堤的洪水一样,冲破种种传统思想的严重束缚,汹涌澎湃,一发不可收拾地向前推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