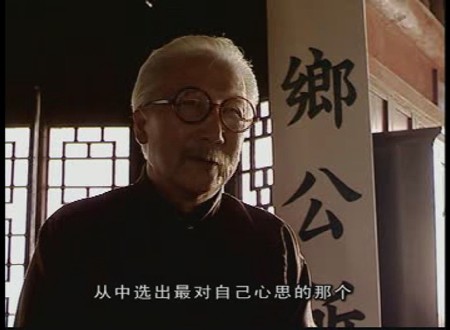|
“保共改良”二十五週年祭 ─評歷史連續劇《走向共和》的美學價值─
辛
灝
年 獻 詞﹕獻給偉大的共和革命――辛亥革命九十二周年
答曰﹕保共改良必死,共和革命必再。
前 言﹕
一位近代史學者在看完了長篇電視歷史劇《走向共和》之後,曾興奮地評價說﹕《走向共和》不啻為── 專制中國的一道閃電, 共和思想的一片霞光; 痛斥改良的一陣狂飆, 呼喚革命的一聲驚雷……
是的,當此中共北京洋教專制復辟政權──依然在拼命效法著大清慈禧皇太后「假改革、真保權」的──「愚民之術」時,《走向共和》》的播放和傳播,和它始被中共「刪除革命、祇播改良」,終被中共徹底禁播禁售的「必然命運」,雖然突顯了中共專制統治者的心慌意亂,卻在海外為驚醒人心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特別是在國內,它實已成為號召再造共和革命、推翻專制復辟的驚天之雷…… 它形像地告訴了我們﹕歷史竟是如此驚人的相似。 它藝術地回答了我們﹕何為專制改良?何為專制復辟?誰才是中華民族的新中國?誰才要真正地「走向共和」?
上篇﹕
一、《走向共和》形像地揭開了「保清改良」
然就大清朝推行專制改良的進程而言,又有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第一階段是謂變法以保大清江山,即為鞏固王朝統治而推行的專制行為之改良;第二階段則是變制先保大清皇權,就是「藉預備立憲以保皇權統治」的改良,其本相,乃是立憲為假,保權為真。 長篇電視歷史劇《走向共和》的編導們、演員們,正是以此作為探索歷史的根本軌跡,將晚清一代有血有淚的「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和晚清朝野用情用命的「改良和革命」,入理入境地表現得至深至美。真實的歷史和藝術的再現,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表演,由此而撼動人心,由此而發人深省,更由此而達到了相當的真理境界和藝術境界,從而將藝術形像對於歷史生活的審美關係,也就是「個別概括一般」的藝術哲學,而不是「個別表現一般」的哲學思考,推升到了一個歷史性的、甚至是「近乎完美」的價值高度。
鏡頭之一﹕ 從改革派大臣到割地賠款大師──李中堂在劇中
《走向共和》的鏡頭,一開場便準確地將焦距對準了李鴻章──這一位顯赫中外的大清朝改革家,卻又將他心血費盡的變法實踐,及其必然失敗的痛心結局,展現在一幕又一幕令人傷心慘目的畫面之上﹕ …… 他曾冒天下之大不諱,設立「海防捐」,以為北洋水師籌措軍費,但是李中堂「賣官」斂來的七百五十萬兩白花花的銀子,卻祇能為太后修園慶壽,而「在昆明湖的湖水裡打了水漂」; 他曾為祇有三發炮彈的「定遠艦」籌措彈費,以備在即的與日海軍大戰,但是,祇需一個南洋奸商為兩朝帝師、軍機大臣、戶部尚書翁同龢出版了一本字帖,戶部僅存的六十萬兩白銀,便為王爺宦官等大小官僚藉為太后修園慶壽之名,貪污瓜分殆盡; 為了北洋水師的軍費,軍權在手、大權在握的他,曾從英國帶回來「腳癢水」、甚至掏出銀票三千兩,以賄賂當朝太監李蓮英,以動太后之顏,卻徒招閹宦之辱; 為說動太后同意他與洋人創辦合資銀行,以解北洋之急,他,一位年逾七十的大臣,居然為太后調飲咖啡,竭盡鞠躬盡瘁之形,然而,祇為「婦人一念」,竟然前功盡棄…… 此後,中日甲武一戰,他的北洋水師終於全軍覆沒,割地賠款更使得大清朝顏面喪盡;他積極和艱難推行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他所深懷的富國強兵之願望,頓時化為一片烏有…… 李中堂,這個在敵國的眼裡雖然「才高勝夷」、卻「生不逢國」的大清宰相,這個走在王朝末世和專制末路之上,曾深懷「富國強兵」之願,籌劃「和戎變法」之策,著眼於「師夷長技以制夷」之術的改革派大吏,這個曾首造了「開國門、學科技,制長艦、造火器,建設經濟特區、開放通商口岸,採取官辦、商辦、官督商辦,施行外資、民資和施行中外合資……」的大刀闊斧改革家,其下場,就是這樣地功勞喪盡,苦勞寒心,徒能做一個在談判桌前冒死與敵國討價還價的「割地賠款大師」,一個不僅被眾口一詞詆罵為「賣國賊」的李二先生,和一個祇能在自己的庭園裡,以抽打「下流坯」來自罵「賣國」的羞憤老人……雖然,他那祇能夠為大清朝做一個「裱糊匠和裝潢大師」的改革開放理論,實在將他對大清朝必將敗亡的認知,早已經沉沉地壓迫在他痛苦、並且是無望的心底……
李鴻掌抽下流坯自嘲﹕你又要去賣國嘍……
鏡頭之二﹕ 是「大人物」,也是小人── 康有為上場之後
幾乎是在展現李鴻章悲劇命運的同時,《走向共和》的編導們,卻又力求深刻地塑造了繼改革開放的實幹家李鴻章之後,呼喊變法最響、變法失敗最速、卻又保皇最烈、反對革命最劇的落第舉人──康有為。 康有為一出場,便言詞尖利,神情倨傲,面對著同樣來京參加科舉考試的未來狀元張謇,他那不可一世的神采,實在很難在觀眾的心裡留下「崇高」的形像。 康有為再出場,卻是在他落第歸家之後,草堂授徒之時。他的狂狷之態雖然未因科考落第而有絲毫改變,但是,他那痛徹心脾的自白,卻將一位「一心要考進滿清專制體制內去改良大清政治而不得」的傳統型知識份子,表現得準確而又深刻。 因皇帝召見,而使得康有為仕途有成,抱負有望。然而,他在對天長笑、快心快意之時,竟能夠豪情一收,臉色沉重而又神情詭異地對弟子粱啟超告誡說﹕「必需與孫文劃清界限……」──保皇改良派的忠君心態,勢利之情,陰騺之心和反對革命之堅決,豈但是盡收觀眾眼底,而且令百年之後的海外知情人「心神黯然難已」…… 他終於能夠施展自己要拯救大清朝的抱負了。朝堂之上,面對滿堂昏潰庸碌的朝臣,他敢言殺;變法之際,眼看后黨將成為變法的阻礙,他敢倒后;然而,變法失敗之時,他卻不敢像譚嗣同那樣,「手持歐刀向天笑,功罪留於後人論」,卻是在對「皇上啊,皇上……」的一聲聲做情作態的哀嚎中,溜之不及,逃無蹤影…… 但是,康在獨自逃往海外之後、華僑難解真情之時,他又假托自己身藏光緒皇帝的「衣帶秘詔」,既要保大清皇上,又要救大清皇上,更要鼓吹非光緒皇帝不可的大清朝君主立憲,其「為虎作倀,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為猶甚……」(孫中山語)。電視劇《走向共和》更用它極富洞察力的藝術處理,將康有為一邊能夠「慷慨流涕哭保皇」、一邊卻能夠「轉臉命梁去斂錢」的兩面性格刻畫得入骨三分。而當康有為竟能對那幾個「演戲本為稻粱謀」的演員們說,「你不過是一個戲子,能夠演我這樣的大人物,還不滿足」的話時,面對著「這位大清朝不要、卻偏要大清朝」的保皇派「大人物」,一個驕狂刻薄酸吝之徒,一九八九年之後的海外觀眾,自然祇能是「欲笑不能」……特別是在檀香山那同一個戲台上,當這些演員轉而演出了另一齣「贊革命而貶保皇」的大戲之後,孫中山先生對這些戲子的平等、同情和傾囊相贈的感人情形,就更將孫、康這兩個人格修養、政治背景完全不同的近代人物,對比得涇渭分明。難怪國學大師章太炎曾揮筆斥康是一個「利祿熏心,為一時之富貴,而甘冒萬億不諱言而不辭的市儈……」 《走向共和》的編導們,不獨對孫康二人及其所代表的歷史和政治內涵,表達了他們鮮明的政治傾向性,猶站在歷史的高度之上,用孫中山先生對李中堂說的話,深入地概括了康有為變法的淺薄內容和缺少見地﹕「康先生想做的事,中堂大人已经做到了,但康先生不想做和不敢做的事情,中堂你也很难做到……」,可謂一針見血。
康有為說服已經遜位的大清朝前攝政王復辟
電視劇還用康有為夜訪分手弟子梁啟超的晦暗畫面,描繪了這個從共和革命前的保皇改良派終於墮落為共和革命後之「保清復辟派」的政治歸宿;更將他身著陳舊的大清官服、俯伏在遜位清廷那冰冷大殿上的醜態,為觀眾留下了一聲不屑的長嘆;證明了所謂「保皇改良」實質上就是「保清改良」之本相。祇不過,他們保皇的目的,是想保住大清的江山不被太后所葬送;是祇希望由大清皇帝自己來實行君主立憲,而不被「共和革命」推翻──這,才是康黨保皇和形形色色保皇派的根本追求。
鏡頭之三﹕ 一代女政治家,一個冥頑難化的末代君主─戲說慈禧
隨著歷史人物的陸續登場和劇情的深入展開,大清王朝的改革開放,終於因為菜市口的刀光血影,大連灣和膠州灣相繼為德國及日本所佔,特別是西太后挾光緒西逃八國聯軍的淒慘命運,還有就是一百七十四位大清官員因洋人逼迫而不得不被誅殺的曠古之恥,方使得因李鴻章的「賣國談判」才揀回了一條老命的慈禧太后,在回鑾之後,乃決心﹕不用康粱,卻要推行康粱的新政;大力改革,定要超過康梁的變法。從而將「變法以保大清江山」的第一階段專制改良,推向了又一個、也是最後一個高潮期。 在這個改革開放的高潮期內,西太后在終於認定「祖宗之法可以變、但三綱五常決不可變」的前提之下,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政。在《走向共和》那一個又一個動人心魄的歷史鏡頭之下,她興學堂,傳西學,「不廢洋人愛古人」,確實為後來的中國留下了不應磨滅的歷史成就,卻因篤信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又將她合理的變法,限死在她那「君為臣綱」的「幾個堅持」之下,從而杜絕了制度性變革的歷史可能。 她開言路,允辦報,開啟了中國民間新聞出版事業發生發展的先河期,但是,祇因她又立下了「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的又一個「堅持」,近代中國民間報業的命運,蓋因她「一個人高興,一國人才能高興」,而命途多舛。 她試法制,辦警局,雖有心改革,卻無心變制。所以,新政中的大清江山,仍然是愛新覺羅的一姓江山;所以,她的法制,便仍然是滿清貴族一家一姓的法制。所以,它的警察局,雖敢待小民如虎狼,卻祇能望王公大臣、貝勒爺們而興嘆。 她練新軍、立軍部,雖然有強國之心、分權之能,祇因他寵信首鼠兩端的袁世凱,竟為袁練就一支近代化的私家之軍,不獨促成了大清江山之迅速覆亡,特別是製造了辛亥之後的長期復辟混戰。 特別是她廢科舉,改官制,雖為已經落後的中國科舉考試制度劃下了歷史的句號,卻又為集中皇權、強化專制、賣官鬻爵和官場腐敗,實質是盡情地玩弄改革,打開了花樣百出的門路,提供了更加廣闊的舞台,從而拉開了滿清王朝統治和大清改革開放的最後一幕﹕新政改革大家袁世凱在法制改革的試點──天津那個嶄新的「法院」裡,為未來的攝政王所表演的那一套「新法制大堂審案」,實在是將慶王父子和袁世凱一伙丑惡以極的貪污賣官罪行,進行了最巧妙但卻是最時髦的掩護……自稱甘為大清皇太后一條「惡狗」、敢於直言相諫的忠臣岑春宣,終於滿面淚水地冒死對西太后說出了「新政的黑暗和腐敗的加劇」,從而為徹底失敗的王朝新政,做了一個最為誠實的交待……
岑春宣向太后說立憲是假的、新政更腐敗
歷史劇的鏡頭,就是這樣地將西太后的新政,錯落有致、而又準確深刻地搖動在觀眾的眼裡和心裡,更將老太后「拍龍案而大怒,迸老淚而哀號」的無可奈何情景,絲絲入扣地表現在風雨如晦的「大清朝」朝廷之上﹕「段芝貴賣妓買官,袁世凱通賄弄權,載振攜妓為妾,奕劻收賄賣官……上下左右,宮裡宮外,串通一氣,枉法徇私,折騰得滿世界都知道。讓洋人看我們大清的立憲,是個什麼東西!?」 然而,這段話固然表現了她椎心、甚至是絕望的痛苦,但是,後來,她那一句「現在祇剩下我們自家人了,可以隨便說說話了」的親情,自然還是讓她的皇子龍孫們有恃而無恐;而她那一句「大清的江山是我的,也是你們的」話,就更祇能使她在大清的江山社稷和大清的天皇貴冑之間,難以抉擇了……因為,沒有了她的那些不爭氣的八旗子弟,江山還是大清的嗎?然而,徒有著這一群不爭氣的「八旗子弟」,大清的江山又焉能「千秋萬代永不變色」?
鏡頭之四﹕ 「立憲全是假的,抓權才是真的」──王朝如此告白
如果說西太后的新政製造了大清朝改革開放的最後高潮期,那末,為救大清,為「籠絡人心」,更為保住愛新覺羅的大清江山,與太后新政互為推動、相互交織的,便是大清朝的「高喊立憲和預備立憲」,從而敷演出了一場「假立憲和真保權」的連台大戲,雖然「一唱三嘆,光彩照人」,卻是「假戲真做,令人扼腕」。 在《走向共和》的歷史鏡頭之下,其第一台大戲,就是在大清朝、保皇黨、直至部份民間知識份子高喊君主立憲的激情聲中,清政府終於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然而,五大臣遊盡歐美和日本歸來時,向老太后報告的立憲好處,竟然是「皇權永固、內亂可彌、外患漸輕」;五大臣和太后在內廷與自己一家人討論立憲的結果,便是「祇要君主立憲,絕不要共和立憲」;而當老太后問及袁世凱,究竟是要日本的實君立憲好、還是要英國的虛君立憲好時,袁世凱則以他獨到的「爹媽君憲論」,雖然哄得老太后對做有實權的「君憲之爹」頗有心儀之想,但卻對光緒猶在而「爹媽難定」,心懷憂戚,從而為大清朝的君主立憲留下了「預備立憲」的「假戲」。 其第二台大戲,就是預備立憲這一齣假戲的熱鬧登場。蓋因「一人高興,才能一國高興」,故而當皇帝猶在、太后專權之時,為太后之終身權力計,立憲祇能預備,不能真行;祇因為民間有所謂「七十三、八十四,今年不走明年去」之說,所以,已經七十三歲高齡的老太后,才在袁世凱知情懂意的諫言之間,為立憲定下了十二年的預備期。因為,待到老太后歸天之時,「她老人家也就管不了身後的滔天洪水了」(劇中人袁世凱語)。
徐錫麟在酷刑之下高喊﹕凡搞假立憲,必來真革命!
其第三台大戲,則是日俄戰爭的結果,乃是蕞爾之邦的立憲國日本,打敗了老大的專制國沙俄。於是,朝野之間要求立憲變制的呼聲日益洶洶。當此之時,為「籠絡人心」計,大清朝乃不得不縮短預備立憲的年限,從十二年到九年,再從九年縮短為六年;為「保大清皇權」計,則面對堅決要求從速立憲的洶洶輿論,終於由滿清貴族「五虎」之一的安徽巡撫恩銘說出了「立憲是假,抓權是真」的肺腑之言,雖然為自己招致了殺身之禍,卻在太后死前死後都不能改變「假立憲、真保權、以苟延江山一統」的專制欲望,甚至假預備立憲之名,設立了兩度「皇族內閣」,雖要「永固皇權」,卻終於「葬送皇權」,大清朝旨在「萬代千秋永不變色」的江山,蓋因武昌城頭的一聲槍響,而傾刻覆亡了……
走出鏡頭、回到當今﹕ 保共改良之必然,與「保趙、保胡」改良之種種……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一旦我們「走出鏡頭,回到當今」,就會發現,歷史竟是如此驚人地相似,當今就是歷史的可怕再現。甚至,要想瞭解當今,祇需一賞該劇。這才恰恰是《走向共和》播出後,「大共朝」朝野震撼不已、「馬列國」人人心領神會,舉國上下鞭韃笑罵之聲不絕於耳之所由來。然而,要想真正瞭解歷史劇《走向共和》的歷史和現實意義,要想真正比較「大清朝」的改革開放和「大共朝」的開放改革,為何如此驚人的相似,和它們雖然是「蕭條異代」、卻又並非「如出一轍」的緣由,就必需瞭解中共北京政權的根本性質和政治特徵,否則,我們不但難以理解這番歷史的「輪迴」慘劇,甚至不能理解「大共朝」較之大清朝更無可能改良成功的命運。 那末,中共北京政權的根本性質和特徵是什麼?答曰﹕第一是洋教政權,因為它實行的是馬列洋教統治,建立了一家「教政合一」的政權;第二是專制政權,因為它已經在中國大陸實行了長達五十四年的殘酷專制統治;第三是一個「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了專制制度的復辟政權,它在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艱難反復歷程中,實現了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的全面復辟和超級復辟。 至於它的特徵,則全世界凡是有專制歷史、並且出現過專制復辟的國家、民族和地區,所共有的四大特征,即﹕強行思想統治、強化專制權力、歸復等級制度、厲行專制鎮壓──「中共北京洋教專制復辟政權」委實是一條不缺,惟有過之而無不及。 祇有在我們明確了中共政權的上述性質和特征之後,我們方能夠明白,為何「大共朝」和大清朝在推行專制改良的思想和手段上乃是驚人的相似?為何「大共朝」在專制改良的深度和廣度上祇能遠不及大清朝?為何今日的改革開放之難、甚至是今日中國要「走向共和」,竟然較之昨日大清國要「走向共和」更難、甚至是難於上青天? 因為,當今中共改革開放的事實是﹕ 大清朝做過的,他們倒是部份地做過了。特別是李中堂的「外需和戎、內需變法」,也就是既要「以夷制夷、拉夷打夷」,更要「開國門、學科技,制長艦、造火器,建設經濟特區、開放通商口岸,採取官辦、商辦、官督商辦,吸引外資、民資和施行中外合資……」──無非如此而已。 大清朝敢做的,他們卻不敢做。尤其是慈禧太后敢於開放言論,允許民間辦報辦刊以宣傳西方的精神文明,直到大清王朝敢於廢除滿族貴族特權等等,中共豈止是不敢為之,甚至還要在世界已經成為「地球村」的今天,以所謂「反對西方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名,恪守那個恰恰是來自西方的反動思想──馬克思主義,固守所謂的「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放手大幹「掛羊頭、賣狗肉」的形形色色勾當,直至以擴大中共馬列黨族貴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特權,變「理應是讓權、分利於民」的改革,為「奪民之權、劫民之利」的瘋狂腐敗,來為它的專制改良「保航開道」…… 大清朝不敢做的,中共倒是敢做得很。因為西太后祇敢在菜市口砍掉六顆敢言敢行變法、特別是敢於「倒后」者的頭顱,並且是在政治改革一百日之後;鄧小平則敢在整個北京城屠城,更敢在全中國傾巢鎮壓所謂參加動亂和暴亂的人民,並且是在政治改革根本就沒有發動之前。至於他們對一切和平異議者與反對者的驅逐和鎮壓,則為大清朝廷不敢幹也不曾想…… 大清朝和「大共朝」乃有著一個共同的「專制改良綱領」,那就是﹕大清朝要的是「保清改良」,「大共朝」要的是「保共改良」。稍有異趣的是﹕大清朝的海外「保」派,為保清,而誓死「保皇反后」;大共朝的海外「保」派,則先要「保趙反鄧」、後要「保江反李」,繼而要「反江保朱」,而今,卻又在嚷嚷著要「保胡溫而反江澤民」了……就「從一而終」的中國傳統道德而言,顯見得是「今人不及古人忠」也……。 自然,如果要當真比較大清朝的「保清改良」派和「大共朝」的「保共改良」派,比較這兩代「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隔代「保清、保共」黨人,他們雖然「都是人家不要的,卻偏偏是要人家的」被遺棄者和被放逐者;但當代的保共黨人,在「保」的理論建設上,還是要比前代高明得多,也複雜得多。因為﹕ 「共產黨是打不倒的,共產黨是無人能夠取代的,共產黨裡面有的是健康力量」──是他們的思想前提和感情基礎。 「告別革命卻不說要告別那一家的革命,否定革命卻不否定自己曾跟著共產黨革了別人一輩子的命,反對革命單單祇要反對孫中山倡導的共和革命和推翻了滿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則表達了他們的愛恨情仇,與共產黨一樣至為明確。 「祇允許說‘結束’一黨專政、絕不允許說‘推翻’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祇敢低吼反對專制、卻絕不允許別人高喊反對共產黨專制。 「在共產黨仍然迷信暴力、並正在用暴力鎮壓人民之時,卻念經一樣地天天嘶喊著‘和平理性非暴力’,以公開為共產黨拉‘偏架’。 「敢於無情地批判與否定中華民族及其民族文化,卻絕不批判與否定馬列黨族和馬列文化;直到為了追尋真正馬列主義天堂和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甚至要未雨綢繆地為共產黨、或勸共產黨改名更姓,以為共產黨‘延年益壽’,以寄望中共自己改良成功,以期待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中國‘千秋萬代’」……就更是將當今‘保共改良’的思想和行為表現得淋灕盡致…… 然而,大清朝祇敢在專制改良中腐敗,「大共朝」卻敢在專制改良中腐爛;大清朝雖然運交王朝統治的末代和專制制度的末路,「大共朝」卻命逢復辟王朝的末世和和國際共產專制復辟勢力的全面崩潰……;大清朝曾遭遇列強的欺侮和凌辱,「大共朝」則欣逢列強要和它做生意、搶市場……但,西太后說過「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鄧小平也說過「中國是塊肥肉,你不來自有人來」──他們雖然一個儒雅,一個惡俗,卻都道出了他們要賴「列強以苟延性命」的秘方。祇是前代的列強用堅船利炮驚醒了清國人民的愛國之心,當代的列強則將人權民主之普世理念,挾裹在進口商品的集裝箱內,引發著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之想。更那堪當今的越洋飛機又要比當年的越洋海船要快得太多。因此,由「時移代遷」所帶來的國際環境的改善,國內民智的復甦,終究要使得保共改良和保清改良一樣,落得個「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共同命運…… 歷史劇《走向共和》非但不著當代世事之一字,非但意味深長地以「張勳復辟了滿清」為「終」,將故事嘎然「終場」在「蘇共建立中共」之前,卻通過歷史的畫面和藝術的形像,親快仇痛地引發了全中國、甚至是全世界華人對他的唏噓感嘆,或者是滿腹驚惶,直至將前後兩代「保清改良」和「保共改良」之已死和必死的黯淡歷史、傷心前景、及其燭影斧聲的歷史「謎底」,全然地揭開在我們國人的心頭。它所激發的歷史創傷和現實創痛,實令人噓呵難止,心神難寧。這究竟是藝術的魅力,還是思想的力量,抑或僅僅是它足以撼動人心的悲劇美,才震撼了中華兒女之心,驚斷了馬列子孫之夢呢?
下篇﹕
《走向共和》藝術地再現了中國共和革命
可以說,歷史劇《走向共和》的觀眾,祇需憑心而觀,誰都能看得出﹕正是大清朝的專制改良,才為她帶來了這樣四個惡果﹕一是專制強化,二是腐敗加劇,三是人心轉向革命,四是王朝危如壘卵。而對這家末世王朝和那個末路的君主專制制度而言, 其致命的一擊,卻是孫中山所倡導的「共和革命」。歷史劇《走向共和》,正是嚴格地以真實的歷史為藍本,實事求是地將專制改良之不能救大清,唯有孫中山的革命才能從根本上推動中國「走向共和」的真理,形像地、藝術地、活靈活現地再現於我們這個「保共改良」的時代。而《走向共和》對中國共和革命勝利發端的熒幕再現,則主要是以孫中山先生倡導和發動共和革命的艱難歷程、初造成功和反對專制復辟之三大歷程為軌跡,從而將一幅幅歷史的畫面交融在當代的人心之中,展現著共和的魅力,激發著革命的思想,凝聚著反復辟的意志,催動著全中國人民的迅速覺醒和徹底覺醒……這才是她深刻難掩的美學價值、即認識意義。
鏡頭之一﹕ 倘若固守專制,那就祇有推翻它
《走向共和》的編導們,因深知要「走向共和」,就必需先有共和的思想;要發動共和革命,就必需先有共和革命的理論;要建立一個真正共和的新中國,就必需先有革命建國的藍圖。而孫中山先生的可貴之處,就是他擁有著「融東西方之進步文明為一體的共和革命理論和民主建國綱領」。所以,他倡導和發動的革命,才能夠因共和思想的潤澤人心,而築起人心的基礎。這不僅在「保清改良乃為天下共擁、反清革命卻遭天下共棄」的艱難發韌之初,是為必需;而且,在辛亥之後中國人民屢遭專制復辟之苦的混亂歲月之中,尤為重要…… 當落第舉人康有為,正在對他的門生們高聲大叫著「無論怎樣忍羞含辱也要考進那個專制體制裡面去」的時候,年輕的孫中山,他的話,卻如沖出山林的一泓清泉,震響在這個專為培養未來保皇改良派的「萬木草堂」裡﹕「若是大清皇帝識大體、知潮流,和平遜位,贊成共和,那是最好的。倘若固守專制,那就祇有推翻它,我們創造一個共和國……」他還這樣地表達了自己的嚮往﹕「无君之共和,才是最純潔的憲政,也是我煌煌华夏,最终要確立的國體……」 他的話,雖然明確而且徹底,但對於那些一心要寄命於大清朝的知識分子來說,卻是「荒唐而且可怕」。那末,什麼是共和呢?孫中山說得好﹕「在現代的共和國家里,‘共’就是說國家權力是公有的,國家的治理,是我們所有國民共同的事業。‘和’就是合群力而治國,就是民主啊……」 在美國舊金山那一處被遺棄的廠房裡,就是在那個連屋頂和牆壁都空空如也的廢墟之上,劇中人孫中山又是這樣明白曉暢地向當地華僑講述了他的三民主義理論﹕「民族主義就是民有主義,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人所可獨佔;民權主義就是民治主義,天下者人人皆有治之之責,亦應負治之之責;民生主義就是民享主義,天下既爲人人所共有,那天下之利權,亦自當人人所共享……」──這樣的主義,它會「過時」嗎?這樣的主義,竟會像極個別號稱是「民運人士」者所糟蹋的那樣──「就是專制主義」嗎?應該說,孫中山先生對共和革命和民主建國之最為突出的貢獻,就是他創立了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學說,並且,必將惠澤百代而難衰…… 而當辛亥革命首造成功之後,不論是在南京那個樸素的臨時大總統府裡,還是後來在北京由袁世凱專為歡迎他而設的豪華國宴上,抑或是在其後一個又一個反對專制復辟的歷史戰場上,「他」,曾面對著「走向共和」的偉大歷史鏡頭,不止一次地諄諄告誡說﹕「共和革命分三期而行:軍政期、訓政期、憲政期……我們共和國所言的訓政,和帝制時代乃至專政時代的訓政是截然不一樣的。須知共和國的皇帝是國民;以五千年被壓迫的奴隸,一旦站立起來讓他們做皇帝,那是定然做不好的。比如說,未來的內閣總理也罷,未來的大總統也罷,他們都是代表國民來行政的,他們就能一下子做好這個代表嗎?我看不一定。所以也必須訓政……」孫中山的這一革命歷程思想,不僅向我們告誡了共和革命所必有的艱難歷程;告訴了我們「訓政絕不是專政、更不是專制復辟」的正確道理;而且告訴了我們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國民黨和蔣介石推行訓政的歷史正確性和現實必要性,和正因訓政不足,訓政未果,才造成了赤禍蔓延中華的曠古之難;特別是告訴了我們,在歷經了「馬列黨族」長達半個世紀的專制復辟統治之後,在中華的好文明和世界的好文化已經被中國的馬列子孫破壞了和隔絕了五十餘年之後,意在完成共和的「訓政」,對於「再造共和革命、推翻專制復辟、重續共和民國、實行三民主義」,該是具有著何等的重要意義…… 當《走向共和》的鏡頭對準著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的國會議員大選之時,足以令人莞爾一笑、甚至使得百年後某些「人士」要尷尬一笑的是,中國國民黨在江蘇常州鄉下的那一場競選活動和競選演說,實在是將百年「國情不宜民主論」,斥之於不堪一擊之間──且看劇中的這一段對白﹕ 孫中山﹕蕭鄉長,……如果有人告訴你,因爲你的孩子不識字,就不需要上學堂,你怎麽說? 蕭鄉長:胡說八道,正因爲不識字,才要上學嚒。 孫中山﹕「對呀,所以有人說,老百姓的素質低,不可實行民權,這就跟孩子不識字就不用上學堂一樣荒唐可笑。」……
蕭鄉長和村民聽孫中山、宋教仁談民主、說競選
還需要作進一步的「解釋」嗎?還需要將當今那些保共改良派們的胡說八道,再拎出來辯論一番嗎?所有看不起孫中山先生、蓄意貶低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理論、對百年前中國共和之成就一百個看不上眼的形形色色「人士」們,難道還要沿著百年前無知的國情論,為確保大共江山,而繼續地來抵制、謾罵和反對當代中國共和革命的再生和再起嗎?來繼續地阻擋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共和的痛苦追求和萬難追求嗎? 正因為《走向共和》的編導們,在中國大陸民間已經歷時二十年的歷史反思成就中,汲取了智慧,他們才會在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之後,在劇中用深情凝重的旁白說道﹕「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廣州起義雖然流產了,但卻從此開始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歷史的評價,該是何等的準確和明確。 也正是因為《走向共和》的編導們衷心地贊成孫中山倡導的共和革命,他們才會一次又一次地用劇中的旁白,根據孫中山先生的原話,將近代中國共和革命「從天下共棄而終於走向天下共擁」的必然歷程,解說得明白曉暢、鏗鏘有力;更將一個不畏生死的共和革命領袖在戰場上的英勇行為,表現得極其地動人心魄…… 孫中山先生不僅是一個共和革命的思想家和理論家,而且是一個共和革命的實踐家和參加者。歷史劇《走向共和》實為他曾首先倡導和親身參加中國的共和革命,留下了如許精彩動人的藝術畫面。這對激發當代中國共和革命的再起,推動中國人民實現「完成共和」的偉大歷史使命,該具有著怎樣的號召力量和榜樣力量!
鏡頭之二﹕ 革命保皇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
毋庸諱言的是,歷史劇《走向共和》,說到底,就是一部「歌頌共和革命、反對保清改良」的長卷史詩。而「革命不是要來的,乃是被逼上梁山」的歷史真理,則為她表現得準確而又深刻。然而,革命為誰所逼?答曰﹕一是「假改革真保權」的大清朝,二是「改良為保大清」的形形色色改良派。其中,祇是因為康有為的保皇改良,聲勢最先,勢頭最劇,名氣最響,欺騙最廣,其「助紂為虐、反對革命,較之滿清王朝為猶勝」,所以,倘若不堅決反對之,則革命便無由可起。所以,因大清朝之一意的「真保權假改革」所製造的瘋狂政經腐敗,雖為發動「共和革命」的根由所在;但,祇因深黯「革命黨何以生?生於政治腐敗」的康、梁保皇黨,仍然要拼命地反對革命,甚至成了「梁山下」的攔路之虎,所以,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之必須和堅決要反對保皇黨,也就理所當然。 歷史劇《走向共和》,祇因抓住了這樣一個要害,才將孫中山為發動共和革命而要堅決反對保皇改良的思想和行為,和那些終以淋灕的鮮血來肯定了孫先生「先見之明」的原改良派人士們要堅決「棄改良而從革命」的重大轉變,聲彩並重、凌厲入心地表現在歷史的畫面之上。 「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電報、電話等物質文明的措施,祇會給國內的貪污腐敗、敲詐勒索打開更加廣闊的門路……。」歷史劇雖然沒有將孫中山先生對大清朝改革開放「成果」的早期判斷,表現在劇中;但對孫中山在檀香山不聽其兄之勸,「非要與保皇黨過不去」的行為,賦予了濃墨重彩──他,孫文,和顏悅色地就嘲笑了那個祇花了兩千美元就向康有為買到了大清朝二品頂戴的「改良之母」,而非「革命之母」;針鋒相對地在同一家戲院裡演出了「反保皇、擁革命」的大戲,更以自己對「戲子」們的無私之德和同胞之情,對比了康有為的私欲和狂妄;聲色俱厲地批評了宣傳共和革命的報紙──《檀香山新報》的主持人們,將共和革命的輿論陣地輕而易舉地就為保皇派所佔領,並口若懸河地當場口述了那一篇批判保皇派「自欺欺人」的著名檄文──他說﹕「天下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夫革命與保皇,理不相容,勢不兩立,而康有爲以一人而持二說,首鼠兩端。其革命屬實,則保皇之必僞。其保皇之屬實,革命之說必僞矣。彼輩保皇爲真保皇,所言革命爲假革命。革命保皇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成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衝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 特別是當日本留學生、立憲改良人士徐錫麟,因乃師粱啟超的鼓勵,而要回國效命於大清朝「專制體制內」的立憲改良「大業」時,孫中山先生則苦心相勸,明確指出了清之立憲乃是欺騙國人而已,猶如當時的法國報紙所言﹕「清政府之立憲,實乃清太后愚民之術……」
孫中山告訴徐錫麟大清立憲是一個騙局,徐不聽…
如果說,孫中山的規勸對一心要回到大清專制體制內去效命的徐錫麟,並無咫尺之功,但回國之後的徐錫麟,卻因目睹政治腐敗,改革盡偽,特別是在他的恩師、大清朝五虎之一的安徽巡撫恩銘,親自對他講出了「立憲全是假的、抓權才是真的」這樣一個「改革真相」之後,徐乃翻然一變,從一個真心實意的大清立憲改良派,變成了一個決心以命相效的共和革命烈士…… 正是在這個「棄改良而從革命」的關鍵發展上,歷史劇《走向共和》,乃用著相當的篇幅和濃郁的悲劇氣氛,表現了和烘托了徐錫麟這個原改良人士刺殺恩銘的重場大戲,更用著那一番長鏡頭,將徐在大堂慘遭酷刑受審時的悲壯之情和英勇氣概,刻畫得令人肝膽俱碎──滿身鮮血的徐錫麟,他那「我佩服孫先生有先見之明」的痛心呼喊,他那「凡搞假立憲,必來真革命」的絕命呼喚,豈止是震撼了刑堂,更震撼了欺盡人心的大清朝廷,猶將他流下的無量鮮血,塗畫出了那一番革命必將取代改良的壯麗前景…… 史載,殘酷的滿清政權不僅處死了先為保清改良家、後為共和革命家的徐錫麟,而且將他破腹挖心,甚至吃掉了他的心肝兩臟……。猶如當時《河南》雜誌所嘆﹕「 嗟夫,預備立憲者,尚不如直其名曰預備殺人流血之直接了當也……」 史載,另一位原立憲改良派、青年壯士吳樾,與徐一樣,不僅棄改良而從革命,而且因執行刺殺清出國考察五大臣的使命,而英勇獻身──在歷史劇《走向共和》的屏幕上,那一節節豪華車廂的轟然被炸,和五大臣被炸傷後的一群狼狽之像,豈但是大快人心,而且同樣是宣告了﹕唯有發動共和革命,才是走向共和的人間真理…… 《走向共和》傳播海外之後,雖然立即就有保共改良人士為密切配合中共的禁播禁售,而攥文老調重彈地指斥「孫中山太莽撞,破壞了大清朝和平改良的可能和前景」,然而,歷史劇《走向共和》卻用徐錫麟、吳樾等原改良人士以鮮血記錄著的歷史,還有就是恩銘和岑春宣們或得意、或痛苦的「自白」,將他們對「大共朝」懷著種種私欲的「忠心」,消音在當代中國共和革命必將再起再勝的「風聲鶴唳」之中……
孫中山先生雖有一句名言,謂「華僑是革命之母」,但是,在歷史劇《走向共和》的劇情發展中,卻一再地和動情地表現了孫文的胞兄孫眉對弟弟從事革命的傾心支持。 在那廣闊而又美麗的牧場上,因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而逃往南洋的孫中山,雖然滿臉鬍茬,衣冠不整,但他那一聲歡快的、卻又是深情無限的叫喊──「哥──」,確乎已經將觀眾的心喊出了一片神往之情…… 在日本中山學堂裡面,當孫中山正在對華僑青年講授我們中國人應當追求自由、民主與平等的共和革命道理時,他的哥哥──孫眉,卻拎著一隻不小的皮箱,從檀香山趕到日本,悄悄地站到了教室的窗前──皮箱裡裝滿的,竟是他未到開春季節就賣掉兩千頭小牛犢所換來的錢,以用作弟弟發動共和革命的經費…… 在沒有了牛、連兩千九百畝的牧場也為弟弟的革命變賣一光之後,還是在檀香山他哥哥的家裡,「色厲內親」的哥哥,最終還是將藏在褲腰帶裡的那一千美元掏出來交給了弟弟,這可是他最後一點做生意的本錢了。然而,《檀香山新報》──一份就要痛斥保皇改良的著名華文報紙,就這樣地誕生在海外…… 孫中山辜負了他的哥哥嗎?「辜負」了,因為,辛亥革命成功,當有人從廣東拍來電報,要他任命其兄為廣東省長時,孫中山親自拍電「否決」了…… 然而,孫中山當真辜負了他的哥哥嗎?當然沒有!因為,哥哥所支持的共和革命,初造成功了!因為,他的弟弟,在革命的十六番寒暑間──坐輪船,便將朋友為他買好的上等艙票換成了最下等的;住旅館,則站在華僑已經為他租定的二十美元一天的豪華旅館櫃台前,要求退錢,轉而去住一美元一天的小旅社;他的哥哥將大把大把的錢給了他,可是他常常都是一文不名,甚至連喝一杯咖啡都要賒賬;特別是當他與宋家的慶齡終於結成連理之時,他祇能從自己當年送給那個小慶齡的鋼筆帽上,褪下那一個小小的金屬環,來作為他贈送給新婚妻子的戒指……。但是,當華僑劇團演出結束後,他不僅將所有捐款都付給了演出了革命戲劇的「革命同志」──他是這樣地稱呼他們,而且祇因捐款稀少,自己又身無分文,而當場取下腕上的手表,將它也送給了演員們……歷史劇《走向共和》就是這樣地根據歷史的記載,將我們前一代共和革命領袖的志氣和操守,深情地、並且是用心地展現在當代的觀眾面前;更將共和革命領袖與共產革命領袖的「深溝巨壑」,甚至是與前代保皇改良黨人、以及當代保共黨人的巨大差異,不著痕跡地對比在「劇情和畫面」之間,令人充滿景仰,亦令人「痛定思痛」……
孫中山的哥哥親自將賣牛的錢送給在日本的弟弟
歷史劇《走向共和》之第五個至為重要的啟示,就是她預言了當代勢將爆發的中國革命,將豈止是一場民主推翻專制的共和革命,而且是一場中華民族誓言要驅除馬列洋教的民族革命。雖然她必須追求和平的方式,但絕不放棄任何革命的形式。而中共五十餘年來遠遠超過滿清專制荼毒的種種血腥手段和欺騙行徑,所早已激起的人心覺醒,所能夠激蕩的革命風暴,勢將從政治、思想、經濟和文化等一切方面埋葬那個已經侮辱、虐待和瘋狂毒殺了我們民族國家五十餘年的洋教專制復辟政權。因為,非如此,我們就絕對沒有可能重新開始「走向共和」,直至最後地「完成共和」。 歷史劇《走向共和》之第六個至為重要的啟示,乃是指出了當代中國的共和革命與辛亥革命的歷史傳承性;指出了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革命建國道路,非但沒有過時,而且恰恰是我們今天必須奮鬥和建設的方向;它甚至啟迪了我們,必須正視當代共和革命所帶來的震撼、所製造的變局、所可能產生的流血或混亂……雖然它們全為中共在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上所一手製造,所長期造就,但卻要我們的人民用理性之手去完成……這個理性,就是孫中山先生的軍政、訓政和憲政的思想,以及這個科學思想在當代「法制化」的實現……
孫中山先生在袁世凱為他舉行的歡迎國宴上談訓政
歷史劇《走向共和》之第七個重要的啟示,就是她熱情甚至是深情地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成果──中華民主共和國,即中華民國;就是她熱情並且是深情地肯定了中國國民黨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為使中國「走向共和」所作出的艱難奮鬥,所流過的無量鮮血;就是她熱情特別是深情地一再表現了,正是孫中山先生和他的革命,才是真正地要「走向共和」的,才是要走向「真共和」的,才是要把我們的國家真正建設成為一個民主共和的現代中國的。所以,「誰是新中國」這一二十世紀的「天問」(說明3),便在《走向共和》那一幅幅璀燦畫面上,得到了解答和證明。所以,我們才敢說,「還我民國,再續共和」,乃具有著的歷史的完全正確性;我們才敢說,中國國民黨的奮鬥,一旦拋開了要推進全中國《走向共和》的歷史使命,它就「不再是中國的國民黨」了……。
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成立大會上致詞
而孫中山先生在歷史劇《走向共和》裡所一再高喊過的「中華民主共和國萬歲」,所一再呼喚過的「民國的前途是光明的」,所一再指出的,「我們本來是共和國,可怎麽一次又一次地出現了封建主義、專制主義的東西,這個問題不解決,專制復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國就永遠是一個泡影……」,就實在為我們推翻專制復辟,重建中華民國,增添了無窮盡的力量…… 總之,歷史劇《走向共和》,她對驚醒當世人心,批判「保共改良」誤國,號召「再造共和革命」以推倒當代「共產革命名義之下的瘋狂專制復辟」,將起到的歷史性影響,委實難以預估。當此之際,自鄧小平決策「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推行了二十五年「保共改良」的中共洋教專制復辟政權,猶將何去何從,雖全在彼一念之間,但是,不管他一念為何,是已經太遲的民主改革,還是決心殘酷地鎮壓即將到來的共和革命,其「保共改良」之必死,其保共鎮壓之必敗,則為天地人心之無疑。這,才是本文雖意在評論歷史劇《走向共和》的美學價值,卻命題謂「保共改良二十五週年祭」的由來。
作者說明﹕ 1、本文所引,均出自歷史劇《走向共和》或《誰是新中國》一書上卷第一章「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發端」。 2、這是本文作者於八十年代從事美學研究的心得,曾在國內大學或文藝界講演,均極受歡迎,即將成書出版。 3、《誰是新中國》一書被一些朋友稱做二十世紀的天問。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成立宣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