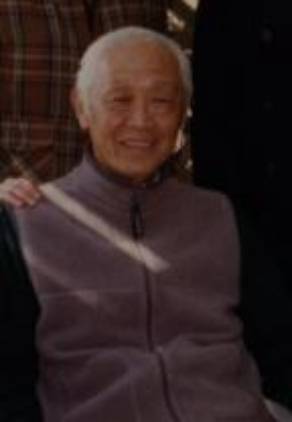一
新亚书院校歌虽只有一百五十一字,但充满真情、充满学问与智慧,同时充满故国之思。要了解体会此校歌的精神,必须了解作者钱宾四师(钱穆先生)创办新亚书院时的心境和他的教育理想。 最能表现宾四师当时心境的,是他于创办新亚书院前后自撰的两部著作的序文。一是民国四十二年(公元一九五三年)二月十日写的宋明理学概述序文中说: “顾余自念,数十年孤陋穷识,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虽居相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成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成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敢忘先儒之榘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所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责,虽数十年光阴浪掷,已如白驹过隙,而幼年童真,犹往来于我心,知天良之未泯──民国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在江南大学,赤氛方炽──感触时变,益多会心。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再度流亡──今年续成此书,此皆十年来大病大乱中所得──”。 宾四师志节之贞烈,不为任何环境所动摇,垂老之年,天良未泯,童心犹存,在这种心情之下,创办新亚书院,所以要了解新亚校歌,必先体会宾四师这种心境。 再读宾四师于民国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所撰庄子纂笺自序述其内心的感触,犹为深切。他说:“报载平津大学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竞相坦白者逾六千人,不禁为之废书掷笔而叹。念蒙叟复生,亦将何以自处?作逍遥之游乎,则何逃于随群 而处禈?齐物论之芒乎,则何逃于必一马之是期;将养其生主乎,则游刃而无地,将处于人间乎,则散木而且剪倏忽无情,混沌必 ,德符虽充,梓梏难解,计惟鼠肝虫臂唯命之从,虽是以为人之宗师乎,又鸟得求曳尾于涂中,又鸟得观鱼于蒙上。天地虽大,将不容此人,而何有乎所谓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然而古人有言:焦头烂额为上客,曲突从薪处下坐。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以蔽之,无亦曰墨翟是而扬米非则已,若尚四十年来漆园之书,尚能索解于人间,将不至有若是。天不丧斯文,后有读者,当知其内心之苦,是甚于考亭之释离骚也”。 可见宾四师之创办新亚书院,用心之苦,是欲为往圣继绝学。此种精神,一一浮现于校歌之中,所以特别指出“人”之尊严,以为斯文之继。如果我们能认知宾四师九十六年庄严的生命,对校歌的了解一定会更深切。 宾四师从十八岁开始,即致力于学术。以后八十年,从事研究、讲学、著述、教育,未尝一日中断。八十年中,学术著作专书八十二种。文章五百余篇。举凡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学史,以致历史地理,无一不遍及。所关涉的问题,都是国史上的重大问题。他学问的广博精深,架构之大,真可谓自南宋朱熹以后八百年中第一人。 民国二十六年(西元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华,中国奋起抗战,初期中国东南沿海沦陷于日寇,国人忧疑大南之将作。宾四师四十四岁着国史大纲,从国史上的大关节处证验中国之必不亡,以振奋人心。当时又有不少知识分子竞逐西风,鄙夷国史,宾四师乃严正指出:“断断无一国之人相率相弃其国史,而其国族犹可以长立于天地间者”。真可谓对当时之知识分子作狮子之吼。 民国七十四年(西元一九八五年)宾四师九十一岁,任台北文化大学博士班导师,六月九日作告别专坛的最后一课。他最后的赠言是:“你们是中国人”。 民国七十九年(西元一九九零年)宾四师九十六岁近去世指前夕对“天人合一”观念更有新的体悟,于是撰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归宿处,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可惜文章未完成,他便溘然长逝。未把他体悟到“天人合一”的新观念完全道出,这是非常可惜的。幸而他指出途辙,将来学者循此途辙,更往前探求,必可得其全貌而供献于世界文化。 宾四师学术多方,而核心则在宋学。他自述说:“自问薄有一得,莫非宋明儒之所赐”。 他的教育理想,亦以宋代的书院制为楷模。 宋代承唐末五代之后,五代是国史上的大黑暗时代──政治败坏、社会残破、学术雕零、思想虚无、道德堕落。人几乎无以自立为人。北宋承此大崩坏之余,学者面对大难,认为要救国族的危难,必须从教育工作挽救人心,使人能恢复人格,然后社会可以重建。所以宋代学者多是教育家,于是书院大兴,莫不以重建人生认为急务。宋代的国势虽不及汉唐之盛,但学术与思想则远超于汉唐。中国文化的统绪乃得以延续。今日中国的情况,有些方面颇似五代。宾四师创办新亚书院,不但要建立学术,同时要建设人生。把宋代书院的精神,寓于现代的大学制度之中。这番理想,表现于他所手订的新亚书院的学规中。 学规第一条: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 第二条: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的最高旨趣在做人。 第十六条:一个活的、完整的人,应该具有多方面的知识。但多方面的知识,不能成为一个活的完整的人,你须在寻求知识中来完成你自己的人格,莫忘失了自己的人格来专为知识而求知识。 第二十二条:起居作息的磨练是事业,喜怒哀乐的反省是学业。 第二十三条:以磨练来坚定你的意志,一反省来修养你的性情,你的意志与性情将会决定你将来学业与事业之一切。 第二十四条:──敬爱你的人格,凭你的学业与人格来贡献于你敬爱的国家与民族,来贡献于你敬爱的人类与文化。 不了解宾四师这番心情,就很难深切地体会校歌的精义。
二
校歌第一节: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心呀精神”。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是何等庄严的景象!它唤起人庄严的情怀。人生有轻快的一面,也必须有庄严的一面,轻快由于感情的流动、洒脱;庄严由于感情的凝定、执着。人生如果全无轻快之情,则人生太凄苦,不足一万满地实践生命。但是,如果只有轻快而无凝定的感情,则人不能挺拔地站起来。因为要听吧地站起来,必先有一定点,才可以立定脚跟,然后可以挺立。所以要挺立,必须有凝定执着的感情。凝定而执着的感情,必须有责任感,责任感是道德与理想的起点,正是人能挺立的起点。所以庄严的感情必不可无。 天地生化万物。万物在天地的怀抱中生生不息,此中实蕴藏无限的仁心。所以天地不是只晨昏昼夜、四时健行。毫无情意的大自然,它同时是重山苍苍、江水泱泱的有情世界。它赋予人感情与睿智,于是人在此苍茫的大地发展出灿烂的“人之文化”。 在人之文化中,不但人均应被尊重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同时每人应自重为一有灵魂的人,不把自己作为工具,也不视别人为工具;不把自己作为追求物欲的工具;不视别人为实现自己物欲的工具。人人就自己才性之所长,开启自己真实的理想,怀一颗敏感的心灵,去接触自己的真生命,过一种真实的“人”的生活。 敏感的心灵常被人世的苦难所触动,于是发愿为救助世人的苦难而奉献心力,此之谓理想。理想是公的,因为希望世间无有苦难是众人心之所同。所以理想有普世的意义与价值。它与欲望不同,因为欲望只是个人的私企求(如权力欲、财富欲、地为欲──等),与理想不同。而世人常误认“欲望”为“理想”,新亚人必应知两者不同而有所抉择。 理想把人的心胸推广,广阔至极的胸襟如张载西铭所说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下之疲癃残疾,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实现理想不但要有广大的胸襟,还要有长远恒久的毅力。因为有价值的事,不会一朝一夕,一蹴而成,所以要实现一个真正的理想,不但要突破一己的私欲,还要突破耐心的限度,长时间对理想保持不厌不倦之情,把生命中最佳的力量奉献出来。 当此举世如狂地追求物欲的今日,我们应有豪杰的气概,独往独来,不与流俗合污为中国文化理想的荷负者。 新亚校歌是新亚精神的赞歌,它要唤醒新亚同人人格的自觉,点醒中国青年真实的生命,以广大的胸襟,远大的目光,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力量献给中国文化的长流。
三
校歌第二节: “十万里,上下四方俯仰锦绣,五千载今来古往一片光明。五万万神明子孙,东海、西海、北海,有圣人。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这是对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最深情的赞叹。如果我们切实回顾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我们不必觉得这是真诚的赞叹。 中国有壮丽的河山,有可歌可泣的历史,有使人仰慕的圣哲,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豪杰行谊,有数不尽优雅动人的文学艺术,有极丰富璀璨的文物,尤其重要的是有一贯串于历史、人物、山河、艺术、文物中之道德精神的文化统绪。她陶冶出中国人特有的生活风格与情调,成为世上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群体。她的宽宏大度能搏合许多族群而成一大民族。所以中国是由历史、文物、山河、艺术、文学、文物所搏合而成的一有机体,她与现在国际上一些缺乏历史文化的军人政权不同。现代不成熟的政治学以为凡具备人民、土地、主权三者就可结构国家。他们只认识国家的体质条件,未认识到国家的精神条件。于是有些军事强人,掠夺了土地,掠夺了人民,自建政权,即僭称为国家。其实他们只是一些政权而已,与中国大不相同。当然,中国在体质条件上亦具备人民、土地、与主权。不过中国的人民,是指有数千年文化素养、具有中国文化气质的人群,不是如政治学上所指的自然人;中国的土地,是历几千年沿革,几千年整理,附着几千年文物的人文地理不同于现代政治学上所指的自然土地;中国历史上的主权观念亦与现代政治学上的主权观不同,现代主权之说是由于近代国际间政权林立,为了保护本土的利益而设计出来的。中国历史上是东亚的最大宗主国,四周围的国家大都是中国的蒲属,各国行事其自主的权力并不互相冲突,所以各国有实际的行政权力,无须狺狺于主权的争辩,所以现代政治学上凭人民、土地、主权三要素而结构成的国家,是浅化的、量化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有深度的、质化的国家。当然中国文化不是全无瑕疵的,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她的弱点。因为文化是由多种因子配合结构而成,当各因子配合得宜,适合环境需求时,文化就表现得光彩夺目。但社会环境不断在改变,当文化的各因子配合失宜,位能随时改变不能与社会环境相适应,便表现暗淡无光。中国近百余年来文化的因子失调,加一长期受非理性的政权所伤害,未能适合近代环境,至内政外交遭遇种种挫折,于是不少人因中国近百年的挫折而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殊不知文化是具有生命的特质,它不断在成长,不断在新陈代谢──剥落腐朽的部分,又吸收养分新生一部分。只要文化生命的生机未断,虽受斫伤,仍可再生。而且民族文化常寓有该民族赖以生存的力量,因为民族文化是该民族在长期奋斗磨练中长成,它的性格必带有一种克服困难的能力。尤其一个历史长远而成熟的文化,它的生命力必是极坚韧的。所以中国经历数千年,曾遭遇不少挫折而终能渡过艰难而挺立于世,此证明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很强健。我们更应进一步认知:文化生活的强弱,在于其成员当时所作贡献的品质与多少而定。贡献不可以空言必来自其生命最真实、最精彩之处。新亚的教育理想,就是点醒人的真实生命,唤醒人真实生命的良知。校歌就是要兴发一颗颗真实的心灵。 但是,有些人对新亚校歌可能仍存有几点怀疑: 一.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极邪恶的人物,怎能说“今来古往一片光明”呢? 二.新亚精神似乎保守性较强,而进步性较弱? 三.新亚特别指出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此是否与当前排斥西方文化的“东方智慧论”相类似? 不清除这几点疑虑,对新亚校歌终难有深入的体悟。 就第一点而言,如果从个人观察,则每人都有弱点与缺点。但是,如果从社会的总体看,则大多数人都盼望社会进步与光明。着大多数人善良的盼望,就是社会能进步的最大力量。因此,人类社会虽有种种罪恶,而人类社会依然在进步,这是人性最大的光辉,同时表示人性本质的善良。所以中国人深信孟子的“性善说”。我们从此处体认,然后可以了解“今来古往一片光明”一语的意义。 就第二点来说,新亚精神似乎保守性较强,而进步性较弱。不错,我们必先认知保守不是一贬词,只是表示一种态度。新亚书院的态度不是抱残守阙,而是要保持原来有价值的精神,为原来有价值的东西拂去它表面的尘埃,使它再焕发光辉。我们必须认识,一切有价值的精神都来自人的真性情,是真性情的流露。所以道德精神是在每个人的身上,在每个人的心中。因此,就道德精神的本质言并无新旧之别,所不同的是表现的方式而已。新亚书院所欲保持的使人的真精神,也是道德的真精神,不是它所表现的方式。试看现在世人所歌颂的道德如人道、人格、正义、诚信……等,何一而非由二千多年来“性善论”所主张“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而来。即使今日所歌颂的政治道德如人格尊严、民主、自由等观念,也无一不与“性善说”想通。试想倘使人性为不善。何有人格尊严可言?倘使人性为不善,如何可以付予民主之权?倘使人性为不善,又将何以寄托此自由之身?道德不会毫无根源而今日突发的,它必有渊源,必本于人性,有人性发育而来。所以今日所患者不是“保守”而是正患不能保守原来有价值的真精神。能保守原来有价值的真精神,然后可以求进步。进步不同于改变,进步是要有价值的理想作为目标。向有价值的理想接近,才是进步,不向有价值的理想接近只是“改变”,不是“进步”。现在世人热心于求“改变”而不求“进步”,正是当前的流行病。新亚书院所追求的是有价值的进步,不是无价值无理想的改变。 至于第三点说新亚书院强调中国文化似乎和当前一些强调“东方智慧”以排斥西方思想者相类似。着点怀疑是对新亚精神最大的误解。当然,中国文化是东方宝贵的智慧。惟其是智慧,所以必非排外的。凡有智慧的文化必不断地吸收新养分以强化其自身。中国的政治观念发展得较慢,亟需吸取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以加速中国政治观念的发展。何况民主自由思想是近代政治思想的精粹,与原来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正相融合哩。只有“反智慧”的文化然后才会排外,中国文化必不排外。 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智慧有二:一是肯定人的价值,所谓“立人极”;二是认取“性善”之说。惟其性善,所以人有最大的价值与意义。所以性善说与“立人极”是相一致的。此不但为中国人所自认,而且认为凡人类都如此,所以宋儒指出四海圣人,此心同,此理同。岂有半点排外的意思。现在排外的人喜欢用“民族大义”作为排外的理据,殊不知讲求民族大义最重要的在健全民族的文化,追求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是讲求民族大义的最重要课题。无论用任何借口,排斥外来文化,都是一种反智慧的行为。新亚创校的精神是继承中国文化的性善说,所以特别标举陆九渊所说东南西北四海圣人心同理通的话。愿新亚人能体认人性的光明,体认文化的光明、历史的光明,即自己内心的光明,更扩而充之。
四
校歌第三节: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一无所有,一无平藉,我们赤手空拳,只有满怀理想,满腔热血。我们把全副生命,为追求理想,投向无尽的未来。因为中国需要新生,人类需要新生。道路虽然险阻,我们不害怕,我们会自我警策,环境虽然困乏,我们不气馁,我们对理想愈见深情。责任维重,道路虽长,我们愿意承担,愿意承担。我们用坚韧的毅力,用强壮的两肩来承担,我们以欢乐的情怀,无怨无尤地去承担。让我们都怀着青春的活力,结队向前,因为我们都是中国文化理想的荷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