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
宣 言
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
牟宗三
徐復觀 張君勱 唐君毅 合撰
本刊編委余健文博士導言﹕
握天樞以爭剝復
──讀「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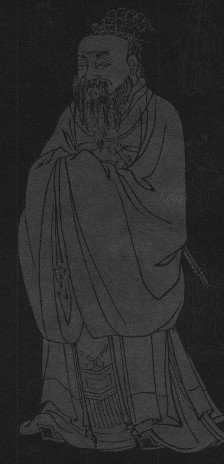 「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由唐君毅先生起草,經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反復修正,後以四人名義聯署發表於一九五八年。其緣起見原編者按語中。五十年來,此文被廣泛徵引,學術界通稱之為「當代新儒家」宣言。此文代表了一代學人以摯深的憂患意識,對中國文化及政治作徹底之反思。故其涵蓋面極廣:由研究中國學術文化之基本應有之態度、中國文化之特性、中西哲學之異同、中國文化之倫理與宗教及心性之學之意義、如何從中國文化中開出民主與科學、由近世中國政治的現實中尋求建立民主制度之途、及世界文化相互學習融通之途。充份表現了四位大師一生之志業與學術成果。五十年後之今日再三讀之,更顯其超越時間的文化精神意義。讀者如能切合今日中國文化認同與民主建國等問題以深思之,定能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進而由之啟發出高遠廣大的理想。 「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由唐君毅先生起草,經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反復修正,後以四人名義聯署發表於一九五八年。其緣起見原編者按語中。五十年來,此文被廣泛徵引,學術界通稱之為「當代新儒家」宣言。此文代表了一代學人以摯深的憂患意識,對中國文化及政治作徹底之反思。故其涵蓋面極廣:由研究中國學術文化之基本應有之態度、中國文化之特性、中西哲學之異同、中國文化之倫理與宗教及心性之學之意義、如何從中國文化中開出民主與科學、由近世中國政治的現實中尋求建立民主制度之途、及世界文化相互學習融通之途。充份表現了四位大師一生之志業與學術成果。五十年後之今日再三讀之,更顯其超越時間的文化精神意義。讀者如能切合今日中國文化認同與民主建國等問題以深思之,定能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進而由之啟發出高遠廣大的理想。
明末以來,中國的學術文化一直處於一種萎縮的狀態中,清末西方文化挾其物質文明之強勢入侵,使此本來已現衰頹之象的文化,全面解體。生於斯世,有良知的知識人多能注意中國文化的問題,有「要改造中國的現實,必須從文化入手」之共同認識。但建設更新文化之途則人見人殊。有人主張以中國固有文化傳統為本、有人提倡全盤西化,然而,數十年來,中國的政局混亂,戰禍不斷,知識人只能用心於現實的政治中,或在社會文化的表層上,作一些通俗文化的改變,一直未能從根本上作深徹的省察。文化的建設只是斷斷續續,在紛爭中遲緩不進。四九年大陸變色,從此十億炎黃子孫生活在專制高壓的統治下,不再有自由之思想,神州大地萬馬齊喑,學術文化被拴於馬列毛之下,全歸於虛無。
大陸之淪於共黨,對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而言,是千年未有的大災難,五十年代一群流亡港台的學人,遭遇此空前之大變局。在「四顧蒼茫,一無憑藉的心境情調下,撫今追昔,從根本上反復用心。」對中國及其文化之淪亡作深切的反省。但他們並沒有悲觀的情緒、更不輕言放棄,他們認為「真正的智慧是生於憂患,因為只有憂患,可以把我們之精神從一種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來,以產生一超越涵蓋的胸襟,去看問題的表面與裡面,來路與去路。」於是他們發大悲願,以重建中華文化、建設民主共和為終身之志。其心境與志業只有明末顧、黃、王等大儒可比。今日的知識份子要真切認識了解此一心願,已復不易得。
五十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在大陸只能講馬列毛,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仍是胡適西化自由主義派的天下。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則以教會為主導,中國文化更備受輕邈。在此艱難孤獨的環境中,這群懷抱共同志向的學者在海外獨樹一幟,以中華文化之傳承為使命,學術界稱他們為「當代新儒家」。「新儒家」之所以為新,並非只是時間上的新,而是在於他們能相應時代的課題,對儒家文化作一深徹的反省,使中國文化有更高更深的發展,令中華民族的客觀精神生命得到充份的表現。「新儒家」學者們首先直下「肯定承認中國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亦懇求研究中國文化者以此為心。他們指出「任何文化,如果真能視之為人類之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則我們首當注目而加以承認的,當是原來理想所具備的有正面價值的方面。」故他們用心於正面的發揚中國文化的道德理想與其正面的價值,以釐清五四以來一般人對中國文化的誤解,企圖扭轉人們由誤解而生的對中國文化的否定與厭惡之情。
「新儒家」學者們肯定中國文化,但他們決非「國粹主義」者,以為東方文化必優於西方,以為西方之文明,中國亦「古已有之」。反之,他們從不諱言中國文化從宋明以來只偏重於道德心性,以至於發展至近代弊端盡顯。在他們早期論著中,很多是批判中國文化之不足處的。如牟宗三先生「認識心之批判」,就指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知性主體之不立,「政道與治道」則批評傳統儒家只有直線之思維,未能曲節的由內聖開外王,至使中國傳統政治有治道而無政道等。對於西方文化之優點,他們多採取欣賞與肯定的態度,更進而將西方現代文明之本源,與中國文化一一相對照,由之而凸顯出中西文化之相異處。如牟宗三先生言,中國文化精神為「綜和盡理」與「綜和盡氣」,而獨缺西方之「分解盡理」之精神,表現於歷史政治上,則中國是「理性的運用表現」,而西方是「理性的架構表現」。然而,「人間需要通過一些架構而實現價值。」故中國文化之建設必有取法於西方文化之特性以充實之,而後方能見其充實之美。
讀過「新儒家」宣言或對「新儒家」學者們略有認識的人都知道,他們非一般人誤解的無條件擁護傳統,而排拒西方文化者,他們反對的是「五四」以來一種激進的事事求新,盲目反中國文化的風潮。如唐君毅先生言,「我們大家都忘了由有所守以求進步,而以保守與進步為相對相反之名,進步為美名,保守為惡名…由此認識之膚淺與差誤,再以變異即進步,遂非至傾水棄兒,偏於共產黨之以進步份子之美名,使天下人陷於中風狂走而不止。」他們是從歷史中以同情了解之心情,見中國文化之不足處,乃在於只重道德主體的建立,而忽略了知性的獨立發展,故中華民族至今未能充分實踐其理想與表現多元的價值。他們從中國文化內在之要求出發,接受吸收西方之長,以改造更新中國文化。其目的正是要將民主人權與科學理性等普世之價值,吸納於中國文化之根本處,擴大貞定吾民族未來之理想,重建中華民族生命之常道。
五四以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們對於中國文化的種種弊端,亦有能以理性的態度作合理的批判者,但更多的卻是本著一種情緒的反應,全面反對中國文化,將中國文化等同於「吸鴉片、纒小足」、一無是處,覺得西方文化處處優於中國,鼓吹「打倒孔家店」,以為中國人應絕棄自己所有而全盤西化,美其名曰「破舊立新」。然而他們見到的只是今日西方科技文明與民主政治的成果,而絕少能用心於西方之所以有今日之成就的歷史傳統。他們這種推倒一切的激進情緒,推至其邏輯的結論,必然是一種物量化的純否定,此即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最終反而間接的幫助了中共專制政權的建立。五十多年的高壓專制,使此等自由主義者有所省悟。本於知識人之良知,他們對專制政權作出強力的批判,並反思其根源與本質。但他們的這種「反思」,往往不能落實到自己身上,對中共的批判,最後又歸結到「中國文化之專制傳統」上。不過他們口稱的「專制傳統」其實並非源自中國文化,而是他們自己對文化的無知,以至將馬列主義之專制本質誤作中國文化之正宗,於是其所謂之反省批判又回到八十年前「五四」時代的原點,說是「重新啟蒙」,其實是在一個圓圈中循還往返,對文化則一無建樹。
相反,「新儒家」學者們面對自己文化之不足處,採取的是一種理性的態度,他們以同情之心正面地去了解認識到中國文化之內部要求,籍此吸收西方文化之精粹,真正開出中西文化會通之正道。這才是一種對自己的歷史文化真誠負責的態度。就一事一物或針對某一種現象作些言辭激烈的批評,又或以犬儒的機智,賣弄小聰明作巧言的譏諷,人人可以為之,卻於事無補。要能就文化現象,作出正面的理解,以改正弊端,進而能夠有所建立,則非至仁大義者,不能為也。「新儒家」學者們雖未能完成此偉業(文化之建設非上百年的努力,不能有成),但他們的確為後來者開創了一條大道。唐君毅先生以其仁者悲憫之情懷,積極闡揚儒家傳統的人文精神,喚起人們的文化意識,道德理性。著述以外,他更與錢穆等先生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在大陸一片摧毀中國文化之嘶殺聲中,於海外艱苦的環境下傳承並發展了中國文化之正宗,為中華文化保留一點血脈,此可謂「盛德大業」也。牟宗三先生表現的是一個大智者的氣質,他在哲學上成果豐碩。他首先指出中國文化傳統中以誠意正心的內聖之道不能直通至治國平天下之外王大業,認為以內聖之學為本以開出現代文明──民主政治與科學理性──必須以「曲通」的方式,由良知之「自我坎陷」,樹立知性主體而後可成就之。他早年的「新外王」三書正是本著其歷史悲情,重建中國文化的道統,並由此開出中國文化之政統與學統。他更以哲學家的識見,重新將魏晉至宋明之中國哲學作詳盡的疏理,正本清源,中國文化之統緒,得以大明於世。最終他以儒家心性之學為本,會通西方康德以來理性主義之大宗,建立了他「道德的形上學」哲學體系,以「智的直覺」達至福德一致的「圓善」之境。如果說唐、牟的學術以哲學思考與建構為主,徐復觀先生的學術方向則重於中國思想史的考證論述,對中國思想史作現代的疏釋。他更以其特殊的實際政治與軍旅生活經驗,以雄健的文風,通過大量的時政雜文,發揚了儒家的人文精神,貞定了民主自由的意識。他發表於報張雜誌的雜文達七百篇,對五十至八十年代初港臺的社會與文化界影響極深。
很多人一直以來有一種印象,以為「新儒家」就是「新權威主義者」,是反西方、反自由人權的「保守主義者」。中國文化與「新儒家」之所以給人此等負面形象,一方面是由於現代的知識人毫無價值意識,以功利之心看文化,以為文化只是現實政治的工具,他們「忘了人類之歷史文化,不同於客觀外在的自然物」,「對一切人間的事物,若是根本沒有同情與敬意,即根本無真實的了解。」對於自己的傳統,他們沒有基本的同情與敬意,故亦不能有真實的理解。另一方面則不能不歸罪於中共「文化黨官」在介紹「新儒家」時束意的扭曲。就此宣言而言,大陸出版的「現代新儒學輯要叢書」:《文化意識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學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收錄此文時,對「敏感」字句任意刪節達十處之多,其中第十節「我們對中國現代政治史之認識」竟全節近四千字被砍掉。此等不作說明的刪節在引介新儒家的書本上,屢見不鮮。
今日中國大陸上馬列主義之幽靈仍在徘徊,但其思想之囚籠已慢慢開始解體,重讀「新儒家」宣言更有特殊的時代意義。由此我們重新認識「新儒家」的志業與理想,正是以平正理性之心,以中國文化為主體,通過中西文化傳統的批判比較來吸收西方文化之優良處,並在現實政治上肯定民主人權之普世價值,以期中華民族更能客觀化其精神生命。「握天樞以爭剝復」,中華民族與其文化剝之將盡而至於一陽來復之幾,正在當下。
二00四年三月十五日
正文﹕
原編者案:此宣言之緣起,初是由張君勱先生去年春與唐君毅先生在美談到西方人士對中國學術之研究方式,及對中國文化與政治前途之根本認識,多有未能切當之處,實足生心害政,遂由張先生兼函在台之牟宗三徐復觀二先生,徵求同意,共同發表一文。後經徐牟二先生讚同,並書陳意見,由唐先生與張先生商後,在美草定初稿,再寄徐牟二先生修正。往復函商,遂成此文。此文初意,本重在先由英文發表,故內容與語氣,多為針對若干西方人士對中國文化之意見而說。但中文定稿後,因循數月,未及迻譯。諸先生又欲轉移西方人士之觀念上之成見,亦非此一文之所能為功。最重要者仍為吾中國人之反求諸己,對其文化前途,先有一自信。故決定先以中文交《民主評論》及《再生》二雜誌之一九五八年之元旦號同時發表。特此致謝。
目 錄
1。前言 ─ 我們發表此宣言之理由。
2。世界人士研究中國學術文化之三種動機與道路及其缺點。
3。中國歷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
4。中國哲學思想在中國文化中之地位及其與西方文化之不同。
5。中國文化之倫理道德與宗教精神。
6。中國心性之學的意義。
7。中國歷史文化所以長久之理由。
8。中國文化之發展與科學。
9。中國文化之發展與民主建國。
10。我們對中國現代政治史之認識。
11。我們對於西方文化之期望,及西方所應學習於東方之智慧者。
12。我們對於世界學術思想之期望。
一、前言 ─ 我們發表此宣言之理由
在正式開始本宣言正文之前,我們要先說明,我們之聯名發出此宣言,曾迭經考慮。首先,我們相信:如我們所說的是真理,則用一人的名義說出,與用數人的名義說出,其真理之價值毫無增減。其次,我們之思想,並非一切方面皆完全相同,而抱大體相同的中西人士,亦並不必僅我們數人。再其次,我們亦相信:一真正的思想運動文化運動之形成,主要有賴於人與人之思想之自然的互相影響後,而各自發出類似的思想。若祇由少數已有某種思想的人,先以文字宣稱其近於定型的思想,反易使此外的人感覺這些思想與自己並不相干,因而造成了這些思想在散佈上的阻隔。但我們從另一方面想,我們至少在對中國文化之許多主張上是大體相同,並無形間成為我們的共信。固然成為一時少數人的共信的,不必即是真理,但真理亦至少必須以二人以上的共信為其客觀的見證。如果我不將已成為我們所共信的主張說出,則我們主張中可成為真理的成份,不易為世人所共見。因此,亦將減輕了我們願為真理向世人多方採證的願望。至於抱有大體相同思想的中西人士,我們在此宣言上未能一一與之聯絡,則為節省書疏往返之繁。但我們絕不願意這些思想只被稱為我們幾個人的思想。這是在此宣言正文之前,應當加以預先聲明的。
在此宣言中,我們所要說的,是我們對中國文化之過去與現在之基本認識及對其前途之展望,與今日中國及世界人士研究中國學術文化及中國問題應取的方向,並附及我們對世界文化的期望。對於這些問題,雖然為我們數十年來所注意,亦為中國及世界無數專家學者政治家們所注意;但是若非八年前中國遭遇此空前的大變局,迫使我們流亡海外,在四顧蒼茫,一無憑藉的心境情調之下,撫今追昔,從根本上反復用心,則我們亦不會對這些問題能認得如此清楚。我們相信,真正的智慧是生於憂患。因為只有憂患,可以把我們之精神從一種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來,以產生一超越而涵蓋的胸襟,去看問題的表面與裡面,來路與去路。
如果世界其他國家的學者們,及十年前的我們,與其他中國學者們,莫有經過同類的憂患,或是同一的超越而涵蓋的胸襟,去看這許多問題,則恐怕不免為一片面的觀點的限制,而產生無數的誤解,因而不必能認識我們之所認識。所以我們必須把我們所認識者,去掉一些世俗的虛文,先後結論上宣告世界,以求世界及中國人士之指教。我們之所以要把我們對自己國家文化之過去現在與將來前途的看法,向世界宣告,是因為我們真切相信:中國文化問題,有其世界的重要性。我們姑不論中國為數千年文化歷史,迄未斷絕之世界上極少的國家之一,及十八世紀以前的歐洲人對中國文化的稱美,與中國文化對於人類文化已有的貢獻。但無論如何,中國現有近於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擺在眼前。這全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之生命與精神,何處寄託,如何安頓,實際上早已為全人類的共同良心所關切。中國問題早已化為世界的問題。如果人類的良心,並不容許用原子彈來消滅中國五億以上的人口,則此近四分之一的人類之生命與精神之命運,便將永成為全人類良心上共同的負擔。而此問題之解決,實繫於我們對中國文化之過去現在與將來有真實的認識。如果中國文化不被了解,中國文化沒有將來,則這四分之一的人類之生命與精神,將得不到正當的寄託和安頓;此不僅將招來全人類在現實上的共同禍害,而且全人類之共同良心的負擔將永遠無法解除。
二、世界人士研究中國學術文化之三種動機與道路及其缺點
中國學術文化之成為世界學術研究的對象,被稱為所謂中國學或漢學已有數百年之歷史。而中國之成為一問題,亦已為百年來之中國人士及世界人士所注意。但是究竟中國學術文化之精神的中心在那裡?其發展之方向如何?中國今日文化問題之癥結何在?順著中國學術文化精神之中心,以再向前發展之道路如何?則百年來之中國人,或有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處,此姑不論。而世界人士之了解中國與其學術文化,亦有因其出發之動機不同,而限於片面的觀點,此觀點便阻礙其作更多方面的更深入的認識。此有三者可說。由此三者,我們可以知道中國文化,並未能真被世界人士所認識,而獲得其在世界上應得的地位。
(一)
中國學術文化之介紹入西方,最初是三百年前耶穌會士的功績。耶穌會士之到中國,其動機是傳教。為傳教而輸入西方宗教教義,及若干科學知識技術到中國。再回歐洲即將中國的經籍,及當時之宋明理學一些思想,介紹至西方。當然他們這些使中西文化交流的功績,都是極大的。但是亦正因其動機乃在向中國傳教,所以他們對中國學術思想之注目點,一方是在中國詩書中言及上帝及中國古儒之尊天敬神之處,而一方則對宋明儒之重理重心之思想,極力加以反對。
此種反對之著作,可以利瑪竇之天主實義,孫璋之性理真詮作代表。他們回到歐洲,介紹宋明儒思想,祇是報導性質,並不能得其要點。故不免將宋明儒思想,只作一般西方當時之理性主義、自然主義、以至唯物主義思想看。故當時介紹至歐洲之宋明思想,恆被歐洲之無神論者、唯物主義者引為同調。照我們所了解,宋明儒之思想,實與當時西方康德以下之理想主義哲學更為接近。但是西方之理想主義者,卻並不引宋明儒為同調。此正由耶穌會士之根本動機是在中國傳教,其在中國之思想戰線,乃在援六經及孔子之教,以反宋明儒、反佛老,故他們對宋明儒思想之介紹,不是順著中國文化自身之發展,去加以了解,而只是立足於傳教的立場之上。
(二)
近百年來,世界對中國文化之研究,乃由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中國門戶逐漸洞開而再引起。此時西方人士研究中國文化之動機,實來自對運入西方,及在中國發現之中國文物之好奇心。例如斯坦因、伯希和等在敦煌所發現之文物所引起之所謂敦煌學之類。由此動機而研究中國美術考古,研究中國之西北地理,中國之邊疆史、西域史、蒙古史、中西交通史、以及遼金元史,研究古代金石甲骨之文字,以及中國之方言、中國文字與語言之特性等,皆由此一動機一串相連。對此諸方面之學問,數十年來中國及歐洲之漢學家,各有其不朽之貢獻。但是我們同時亦不能否認,西方人從中國文物所引起之好奇心,及到處走發現、收買、搬運中國文物,以作研究材料之興趣,並不是直接注目於中國這個活的民族之文化生命、文化精神之來源與發展之路向的。此種興趣,與西方學者,要考證已死之埃及文明、小亞細亞文明、波斯文明,而到處去發現、收買、搬運此諸文明之遺物之興趣,在本質上並無分別。而中國清學之方向,原是重文物材料之考證。直到民國,所謂新文化運動時整理國故之風,亦是以清代之治學方法為標準。中西學風,在對中國文化之研究上,兩相湊泊,而此類之漢學研究,即宛成為世界人士對中國文化研究之正宗。
(三)
至最近一二十年之世界對中國文化學術之研究,則又似發展出一新方向,此即對於中國近代史之興趣。此種興趣,可謂由中日戰爭及中國大陸之赤化所引起。在中日戰爭中,西方顧問及外交界人士之來中國者,今日即多已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之領導人物。此種對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動機,其初乃由西方人士與中國政治社會之現實的接觸,及對中國政治與國際局勢之現實的關係之注意而引起。此種現實的動機,與上述由對文物之好奇心,而作對文物之純學術的研究之動機,正成一對反。而此種動機,亦似較易引起人去注意活的中華民族之諸問題。但由現實政治之觀點,去研究中國歷史者,乃由今溯古,由流溯源,由果推因之觀點。當前之現實政治在變化之中,如研究者對現實政治之態度,亦各不一致,而時在變化之中。如研究者之動機,僅由接觸何種之現實政治而引起,則其所擬定之問題,所注目之事實,所用以解釋事實之假設,所導向之結論,皆不免為其個人接觸某種現實政治時之個人之感情,及其對某種現實政治之主觀的態度所決定。此皆易使其陷於個人及一時一地之偏見。欲去此弊,則必須順中國文化歷史之次序,由古至今,由源至流,由因至果之逐漸發展之方向,更須把握中國文化之本質,及其在歷史中所經之曲折,乃能了解中國近代史之意義,及中國文化歷史之未來與前途。由此以研究近代史,則研究者必須先超越其個人對現實政治之主觀態度,並須常想到其在現實政治中所接觸之事實,或只為偶然不重要之事實,或只為在未來歷史中即將改變之事實,或係由中國文化所遇之曲折而發生之事實。由是而其所擬定之問題,當注目之事實,及用以解釋事實之假設,與導向之結論,皆須由其對中國文化歷史之整個發展方向之認識,以為決定。然因世界漢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史之興趣,本多由其對中國政治社會之現實的接觸,及對中國政治與國際局勢之現實關係之注意而起,則上述之偏弊,成為在實際上最難除去者。我們以上所說,並無意否認根據任何動機,以從事研究中國學術文化史者所作之努力,在客觀上之價值。此客觀價值亦儘可超出於其最初研究時之主觀動機之外。而研究者在其研究過程中,亦可不斷然改變其原來之主觀動機。但是我們不能不說此諸主觀動機,在事實上常使研究者只取一片面的觀點去研究中國之學術文化,而在事實上亦已產生不少對於中國學術文化之過去現在與未來之誤解。故我們不能不提出另一種研究中國學術文化動機與態度,同時把我們本此動機與態度去研究所已得的關於中國學術文化之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結論,在大端上加以指出,以懇求世界人士的注意。
三、中國歷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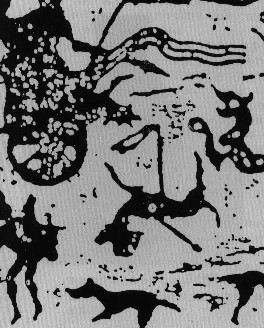 我們首先要懇求:中國與世界人士研究中國學術文化者,須肯定承認中國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我們不能否認,在許多西方人與中國人之心目中,中國文化已經死了。如斯賓格勒,即以中國文化到漢代已死。而中國五四運動以來流行之整理國故之口號,亦是把中國以前之學術文化,統於一「國故」之名詞之下,而不免視之如字紙簍中之物,只待整理一番,以便歸檔存案的。而百年來中國民主建國運動之著著失敗,及今十分之九的中國人之在列寧斯大林之像前緘默無言,不及十分之一的中國人之漂流於臺灣孤島及海外,更似客觀的證明中國文化的生命已經死亡,於是一切對中國學術文化之研究,皆如只是憑弔古蹟。這一種觀念,我們首先要懇求大家將其去掉。我們不否認,百年來中國民主建國運動之著著失敗,曾屢使愛護中國的中國人士與世界人士,不斷失望。我們亦不否認,中國文化正在生病,病至生出許多奇形怪狀之贅瘤,以致失去原形。但病人仍有活的生命。我們要治病,先要肯定病人生命之存在。不能先假定病人已死,而只足供醫學家之解剖研究。至於要問中國文化只是生病而非死亡之證據在那裡?在客觀方面的證據,後文再說。但另有一眼前的證據,當下即是。就是在發表此文的我們,自知我們並未死亡。如果讀者們是研究中國學術文化的,你們亦沒有死亡。如果我們同你們都是活的,而大家心目中同有中國文化,則中國文化便不能是死的。在人之活的心靈中的東西,縱使是已過去的死的,此心靈亦能使之復活。人類過去之歷史文化,亦一直活在研究者的了解,憑弔,懷念的心靈中。這個道理,本是不難承認的極平凡的道理。亦沒有一個研究人類過去歷史文化的人,不自認自己是活人,不自認其所著的書,是由他的活的生命心血所貫注的書,不自認其生命心血之貫注處;一切過去的東西,如在目前。但是一個自以為是在用自己之生命心血,對人類過去之歷史文化作研究者,因其手邊只有這些文物,於是總易忘了此過去之歷史文化之本身,亦是無數代的人,以其生命心血,一頁一頁的寫成的;總易忘了這中間有血,有汗,有淚,有笑,有一貫的理想與精神在貫注。因為忘了這些,便不能把此過去之歷史文化,當作是一客觀的人類之精神生命之表現。遂在研究之時,沒有同情,沒有敬意,亦不期望此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能繼續的發展下去,更不會想到,今日還有真實存在於此歷史文化大流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正在努力使此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繼續發展下去,因而對之亦發生一些同情和敬意。這些事,在此種研究者的心中,認為是情感上的事,是妨礙客觀冷靜的研究的,是文學家,政治宣傳家,或渲染歷史文化之色彩的哲學家的事,不是研究者的事。但是這種研究者之根本錯誤就在這裡。這一種把情感與理智割裂的態度,忽略其所研究之歷史文化,是人類之客觀精神生命之表現的態度,正是緣於此種研究者之最大的自私,即只承認其研究工作中有生命有心血,此外皆無生命無心血。此是忘了人類之歷史文化,不同於客觀外在的自然物而只以對客觀外在之自然物之研究態度,來對人類之歷史文化。此是把人類之歷史文化,化同於自然界的化石。這中間不僅包含一道德上的罪孽,同時也是對人類歷史文化的最不客觀的態度。因為客觀上的歷史文化,本來自始即是人類之客觀精神生命之表現。我們可以說,對一切人間的事物,若是根本沒有同情與敬意,即根本無真實的了解。因一切人間事物之呈現於我們之感覺界者,只是表象。此表象之意義,只有由我們自己的生命心靈,透到此表象之後面,去同情體驗其依於什麼一種人類之生命心靈而有,然後能有真實的了解。我們要透至此表象之後面,則我們必須先能超越我們個人自己之主觀的生命心靈,而有一肯定尊重客觀的人類生命心靈之敬意。此敬意是一導引我們之智慧的光輝,去照察了解其他生命心靈之內部之一引線。只有此引線,而無智慧之運用,以從事研 我們首先要懇求:中國與世界人士研究中國學術文化者,須肯定承認中國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我們不能否認,在許多西方人與中國人之心目中,中國文化已經死了。如斯賓格勒,即以中國文化到漢代已死。而中國五四運動以來流行之整理國故之口號,亦是把中國以前之學術文化,統於一「國故」之名詞之下,而不免視之如字紙簍中之物,只待整理一番,以便歸檔存案的。而百年來中國民主建國運動之著著失敗,及今十分之九的中國人之在列寧斯大林之像前緘默無言,不及十分之一的中國人之漂流於臺灣孤島及海外,更似客觀的證明中國文化的生命已經死亡,於是一切對中國學術文化之研究,皆如只是憑弔古蹟。這一種觀念,我們首先要懇求大家將其去掉。我們不否認,百年來中國民主建國運動之著著失敗,曾屢使愛護中國的中國人士與世界人士,不斷失望。我們亦不否認,中國文化正在生病,病至生出許多奇形怪狀之贅瘤,以致失去原形。但病人仍有活的生命。我們要治病,先要肯定病人生命之存在。不能先假定病人已死,而只足供醫學家之解剖研究。至於要問中國文化只是生病而非死亡之證據在那裡?在客觀方面的證據,後文再說。但另有一眼前的證據,當下即是。就是在發表此文的我們,自知我們並未死亡。如果讀者們是研究中國學術文化的,你們亦沒有死亡。如果我們同你們都是活的,而大家心目中同有中國文化,則中國文化便不能是死的。在人之活的心靈中的東西,縱使是已過去的死的,此心靈亦能使之復活。人類過去之歷史文化,亦一直活在研究者的了解,憑弔,懷念的心靈中。這個道理,本是不難承認的極平凡的道理。亦沒有一個研究人類過去歷史文化的人,不自認自己是活人,不自認其所著的書,是由他的活的生命心血所貫注的書,不自認其生命心血之貫注處;一切過去的東西,如在目前。但是一個自以為是在用自己之生命心血,對人類過去之歷史文化作研究者,因其手邊只有這些文物,於是總易忘了此過去之歷史文化之本身,亦是無數代的人,以其生命心血,一頁一頁的寫成的;總易忘了這中間有血,有汗,有淚,有笑,有一貫的理想與精神在貫注。因為忘了這些,便不能把此過去之歷史文化,當作是一客觀的人類之精神生命之表現。遂在研究之時,沒有同情,沒有敬意,亦不期望此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能繼續的發展下去,更不會想到,今日還有真實存在於此歷史文化大流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正在努力使此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繼續發展下去,因而對之亦發生一些同情和敬意。這些事,在此種研究者的心中,認為是情感上的事,是妨礙客觀冷靜的研究的,是文學家,政治宣傳家,或渲染歷史文化之色彩的哲學家的事,不是研究者的事。但是這種研究者之根本錯誤就在這裡。這一種把情感與理智割裂的態度,忽略其所研究之歷史文化,是人類之客觀精神生命之表現的態度,正是緣於此種研究者之最大的自私,即只承認其研究工作中有生命有心血,此外皆無生命無心血。此是忘了人類之歷史文化,不同於客觀外在的自然物而只以對客觀外在之自然物之研究態度,來對人類之歷史文化。此是把人類之歷史文化,化同於自然界的化石。這中間不僅包含一道德上的罪孽,同時也是對人類歷史文化的最不客觀的態度。因為客觀上的歷史文化,本來自始即是人類之客觀精神生命之表現。我們可以說,對一切人間的事物,若是根本沒有同情與敬意,即根本無真實的了解。因一切人間事物之呈現於我們之感覺界者,只是表象。此表象之意義,只有由我們自己的生命心靈,透到此表象之後面,去同情體驗其依於什麼一種人類之生命心靈而有,然後能有真實的了解。我們要透至此表象之後面,則我們必須先能超越我們個人自己之主觀的生命心靈,而有一肯定尊重客觀的人類生命心靈之敬意。此敬意是一導引我們之智慧的光輝,去照察了解其他生命心靈之內部之一引線。只有此引線,而無智慧之運用,以從事研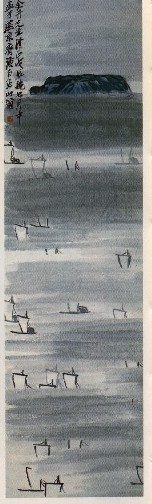 究,固然無了解。但是莫有此敬意為引線,則我們將對此呈現於感覺界之諸表象,只憑我們在主觀上之習慣的成見加以解釋,以至憑任意聯想或偶發奇想加以解釋。這就必然產生無數的誤解,而不能成就客觀的了解。要成就此客觀的了解,則必須以我們對所欲了解者的敬意,導其先路。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的運用,亦隨之增加一分,了解亦隨之增加一分。敬意之伸展在什麼地方停止,則智慧之運用,亦即呆滯不前,人間事物之表象,即成為祇是如此如此呈現之一感覺界事物,或一無生命心靈存在於其內部之自然物;再下一步,便又只成為憑我們主觀的自由,任意加以猜想解釋的對象,於以產生誤解。所以照我們的意思,如果任何研究中國之歷史文化的人,不能真實肯定中國之歷史文化,乃係無數代的中國人,以其生命心血所寫成,而為一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因而多少寄以同情與敬意,則中國之歷史文化,在他們之前,必然只等於一堆無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石。然而由此遽推斷中國文化為已死,卻係大錯。這只因從死的眼光中,所看出來的東西永遠是死的而已。然而我們仍承認一切以死的眼光看中國文化的人,研究中國文化的人,其精神生命是活的,其著的書是活的精神生命之表現。我們的懇求,只是望大家推擴自己之當下自覺是活的之一念,而肯定中國之歷史文化,亦是繼續不斷的一活的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則由此研究所得的結論,將更有其客觀的意義。如果無此肯定,或有之而不能時時被自覺的提起,則一切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皆似最冷靜客觀,而實則亦可能祇是最主觀的自由任意的猜想與解釋,在根本上可完全不能相應。所以研究者切實把自己的研究動機,加以反省檢討,乃推進研究工作的重大關鍵。 究,固然無了解。但是莫有此敬意為引線,則我們將對此呈現於感覺界之諸表象,只憑我們在主觀上之習慣的成見加以解釋,以至憑任意聯想或偶發奇想加以解釋。這就必然產生無數的誤解,而不能成就客觀的了解。要成就此客觀的了解,則必須以我們對所欲了解者的敬意,導其先路。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的運用,亦隨之增加一分,了解亦隨之增加一分。敬意之伸展在什麼地方停止,則智慧之運用,亦即呆滯不前,人間事物之表象,即成為祇是如此如此呈現之一感覺界事物,或一無生命心靈存在於其內部之自然物;再下一步,便又只成為憑我們主觀的自由,任意加以猜想解釋的對象,於以產生誤解。所以照我們的意思,如果任何研究中國之歷史文化的人,不能真實肯定中國之歷史文化,乃係無數代的中國人,以其生命心血所寫成,而為一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因而多少寄以同情與敬意,則中國之歷史文化,在他們之前,必然只等於一堆無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石。然而由此遽推斷中國文化為已死,卻係大錯。這只因從死的眼光中,所看出來的東西永遠是死的而已。然而我們仍承認一切以死的眼光看中國文化的人,研究中國文化的人,其精神生命是活的,其著的書是活的精神生命之表現。我們的懇求,只是望大家推擴自己之當下自覺是活的之一念,而肯定中國之歷史文化,亦是繼續不斷的一活的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則由此研究所得的結論,將更有其客觀的意義。如果無此肯定,或有之而不能時時被自覺的提起,則一切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皆似最冷靜客觀,而實則亦可能祇是最主觀的自由任意的猜想與解釋,在根本上可完全不能相應。所以研究者切實把自己的研究動機,加以反省檢討,乃推進研究工作的重大關鍵。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