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鄒容的《革命軍》
章太炎的《駁康有為書》
和
蘇報案
大陸
金沖及、胡繩武
編者按:本文摘錄於金沖及和胡繩武先生的《辛亥革命史稿》。該文真實地記述了中國共和革命之所以爆發的思想原因和歷史由來。是一篇信史。但由於文中存在著馬列思想的太多浸染,諸如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說教,和指中國的辛亥共和革命是所謂的資產階級革命等等,雖為作者的不得已,但本刊在發表時,還是予以了必要的刪節。敬請作者原諒。
正當留日學生中的拒俄運動進入高潮的時候,革命思潮在國內也迅速高漲起來。這個高漲的起點,是剛從日本歸國的留學生鄒容所寫的《革命軍》一書在上海的出版。
鄒容,原名紹陶,字威丹,四川巴縣人,他的父親鄒子璠是個商人。容幼年時,就很有反叛性。十二歲時,第一次參加考試,就因同考官頂撞而退出試場。他對父親說過:「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愛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戊戌變法時,容年十三,隨日本人學和文。「容因此得識諸學門徑,習聞歐理緒餘,乃瀏覽種種新籍時報,每有所刺激,好發奇辟可駭之論,又縱談時事,人因是以謠言局副辦呼之。無少長貴賤,如其人腐敗,或議有不合,容必面斥之。」一九零一年夏,他到成都考取官費留學日本。他回家時,給大哥蘊丹寫信,痛斥科舉制度:「近國家掇難,而必欲糜費千百萬之國帑,以與百千萬帖括、卷折、考據、詞章之輩中,而揀其一二尤者,於天下國家,何所裨益?」並勸他大哥:「其從事於崇實致用之學,以裨於人心食道也可。」當他準備留日時,他的舅父劉華廷阻撓他說「中國之弱,乃是天運。」「汝一人豈能挽回?」「若裕為國,試看譚嗣同將頭切去,波及父母,好否自知。」鄒容在離家到日本後,給他父母去信時,斷然表示:「人人俱畏死,則殺身成仁無可言。」祇要正義所在,「雖粉身碎骨不計,乃人之義務也。」
 一九二零年春,鄒容到達日本東京,進入同文書院學習.「容在蜀時,既有所感觸,及東來,日受外界刺激,胸懷憤懣,愈難默弭」,思想更趨激進。凡留學生集會時,他常爭先演說,言詞犀利悲壯。那時,駐日南洋學生監督姚文甫是清朝政府的忠實走狗,經常排斥和迫害留日愛國學生。馬君武不能入成城學校,劉成禺不能入聯隊,都是他出的主意,「人言籍籍」,「多歸怒於姚」。一九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鄒容和張繼、翁浩、王孝縝、陳由已五人,乘姚文甫有奸私事,排闥直入,持剪刀剪斷了他的辮髮。把姚辮懸掛留學生會館,並在旁寫到:「南洋學生監督、留學生公敵姚某某辮。」四月間,他因此被迫回國。回到上海後,住在愛國學社,和章太炎同寓。與章太炎、章行嚴、張繼十分投合,結為兄弟。這時,正值拒俄運動開始高漲。四月二十七日,他參加了愛國學社在張園召開的拒俄大會。會後,馮鏡如等發起組織中國四民總會。四月三十日,四民總會集會,各界一千二百多人參加。蔡元培、馬君武等在會上發表演說。會議決定改名國民總會,「以保全國國土國權為目的」,鄒容簽名入會。接著,他又發起成立中國學生同盟會。國民公會成立不久,內部就發生了分化。康有為的門徒龍澤厚和發起人之一的馮鏡如,把它改名國民議政會,計劃以七月九日為陳請西太后歸政光緒的日子。鄒容十分憤怒,帶頭痛罵馮鏡如,愛國學社學生紛紛脫會,國民議政會無形解散。《革命軍》這部著作,從鄒容自序中的說法來看,大體是在日本時寫成的。一九零三年五月,由上海大同書局印行。上海出版的《蘇報》在六月九日刊登了章行嚴的《介紹革命軍》和署名「愛讀《革命軍》者」的《讀革命軍》,六月十日又刊登了章太炎的《革命軍序》。 一九二零年春,鄒容到達日本東京,進入同文書院學習.「容在蜀時,既有所感觸,及東來,日受外界刺激,胸懷憤懣,愈難默弭」,思想更趨激進。凡留學生集會時,他常爭先演說,言詞犀利悲壯。那時,駐日南洋學生監督姚文甫是清朝政府的忠實走狗,經常排斥和迫害留日愛國學生。馬君武不能入成城學校,劉成禺不能入聯隊,都是他出的主意,「人言籍籍」,「多歸怒於姚」。一九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鄒容和張繼、翁浩、王孝縝、陳由已五人,乘姚文甫有奸私事,排闥直入,持剪刀剪斷了他的辮髮。把姚辮懸掛留學生會館,並在旁寫到:「南洋學生監督、留學生公敵姚某某辮。」四月間,他因此被迫回國。回到上海後,住在愛國學社,和章太炎同寓。與章太炎、章行嚴、張繼十分投合,結為兄弟。這時,正值拒俄運動開始高漲。四月二十七日,他參加了愛國學社在張園召開的拒俄大會。會後,馮鏡如等發起組織中國四民總會。四月三十日,四民總會集會,各界一千二百多人參加。蔡元培、馬君武等在會上發表演說。會議決定改名國民總會,「以保全國國土國權為目的」,鄒容簽名入會。接著,他又發起成立中國學生同盟會。國民公會成立不久,內部就發生了分化。康有為的門徒龍澤厚和發起人之一的馮鏡如,把它改名國民議政會,計劃以七月九日為陳請西太后歸政光緒的日子。鄒容十分憤怒,帶頭痛罵馮鏡如,愛國學社學生紛紛脫會,國民議政會無形解散。《革命軍》這部著作,從鄒容自序中的說法來看,大體是在日本時寫成的。一九零三年五月,由上海大同書局印行。上海出版的《蘇報》在六月九日刊登了章行嚴的《介紹革命軍》和署名「愛讀《革命軍》者」的《讀革命軍》,六月十日又刊登了章太炎的《革命軍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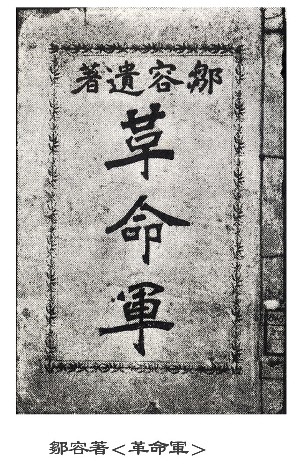 《革命軍》這部著作,在中國近代思想發展史上佔著十分突出的地位。這不僅由於它以通俗曉暢、痛快淋漓的筆墨宣傳革命思想,易於為群眾所接受,從而產生了極為巨大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統地、旗幟鮮明地宣傳民主思想、共和革命和號召創建人民共和國的著作。 《革命軍》這部著作,在中國近代思想發展史上佔著十分突出的地位。這不僅由於它以通俗曉暢、痛快淋漓的筆墨宣傳革命思想,易於為群眾所接受,從而產生了極為巨大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統地、旗幟鮮明地宣傳民主思想、共和革命和號召創建人民共和國的著作。
一打開《革命軍》這本書,劈頭就可以讀到鄒容熱情洋溢的對革命的讚頌:
「有起死回生、還魂返魂、出十八層地獄、升三十三天堂、鬱鬱勃勃、莽莽蒼蒼、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於是沿萬里長城,登昆侖,遊揚子江上下,溯黃河,豎獨立之旗,撞自由之鍾。呼天籲地,破顙裂喉以鳴於我同胞前曰:嗚呼!我中國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國今日欲脫滿洲人之羈縛,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並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長存於二十世紀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為地球上名國、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無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實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養相生活於革命也。我今大聲疾呼,以宣佈革命之旨於天下。」
我們不妨作一些比較:在鄒容之前,孫中山自然是有明確的共和革命思想的,他所領導的革命武裝起義的實際活動,也已經在全國人民中產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但他自己到這時為止,一直還沒有寫出比較系統的宣傳革命思想的著作,興中會的機關報-《中國日報》又因短於學理,不為人所重;一九零一年的《國民報》是有革命傾向的,但它這種傾向常常以隱晦曲折的方式來表達,沒有正面地響亮地喊出革命的口號;《江蘇》雜誌上《革命其可免乎》等文章的發表,已在《革命軍》出版以後。像這樣旗幟鮮明地高舉起革命的旗幟,痛快淋漓,毫不吞吞吐吐地鼓吹革命主張的著作,《革命軍》應該算是第一部。它在當時許多人看來,確實有著石破天驚、振聾發聵的意義,使人耳目為之一新。
鄒容在《革命軍》中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思想。他響亮地喊出:「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他寫到:「夫人之愛其種也,必其內有所結,而後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結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繼焉自結其鄉族,以排他鄉族;繼焉自結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終焉自結其國族,以排他國族。此世界人種之公理,抑以人種發展歷史之一大原因也。」
 他把中國當前的民族問題,集中到「反滿」這一點上來,並從三個方面鼓動人們「反滿」的情緒:第一,引證《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所載的歷史事實,提出「父兄之仇不報,而猶厚顏以事仇人」,「曾祖若有靈,必當不名目於九泉」,來重新激起人們「為父兄報仇」的舊仇。第二,從現實生活中,列舉少數滿人專有行政官之半額、八旗駐防各省以防漢人、八旗子弟有自然俸祿等事實,來說明滿漢兩族待遇的不平等,以激發人們的「不平」。第三,從清政府的對外態度中,以上諭中的「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等語來揭露他們賣國媚外的面目,以燃起人們的新恨。從而,要求人們「張九世復仇之義,作十年血戰之期」。推翻清朝政府,「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恢復漢族的國家。 他把中國當前的民族問題,集中到「反滿」這一點上來,並從三個方面鼓動人們「反滿」的情緒:第一,引證《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所載的歷史事實,提出「父兄之仇不報,而猶厚顏以事仇人」,「曾祖若有靈,必當不名目於九泉」,來重新激起人們「為父兄報仇」的舊仇。第二,從現實生活中,列舉少數滿人專有行政官之半額、八旗駐防各省以防漢人、八旗子弟有自然俸祿等事實,來說明滿漢兩族待遇的不平等,以激發人們的「不平」。第三,從清政府的對外態度中,以上諭中的「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等語來揭露他們賣國媚外的面目,以燃起人們的新恨。從而,要求人們「張九世復仇之義,作十年血戰之期」。推翻清朝政府,「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恢復漢族的國家。
鄒容提出的革命的內容,不祇是民族主義這一個方面。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比過去其它人更加鮮明地、系統地宣傳了民主共和國的理想。
他從國民的天賦權利這一觀點出發來提出問題。寫到:「今試問儕何為而革命?必有障礙吾國民天賦權利之惡魔焉,吾儕得而掃除之,以複我天賦之權利。」「有生之初,無人不自由,即無人不平等,初無所謂君也,所謂臣也。」「後世之人,不知此義,一任無數之民賊獨夫,大盜巨寇,舉眾人所有而獨有之,以為一家一姓之私產,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無一平等,無一自由。」他還說:「自世界文明日開,而專制政體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故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殺盡專制我之君主,以複我天賦之人權」。
他還進一步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具體方案,如:「定名中華共和國」;「建立中央政府為全國辦事之總機關」:「中投票公舉一總議員,由各省總議員中投票公舉一人為暫行大總統,為全國之代表人」;「全國無論男女,皆為國民」;「凡為國人,男女一律平等,無上下貴賤之分」;「人不可奪之權利,皆由天授」;「無論何時,政府所為,有干犯人民權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舊日之政府。」這自然是比較徹底的民主共和思想了。
鄒容在全書最後,響亮地高呼:「中華共和國萬歲!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像這樣旗幟鮮明地宣傳民主共和國的理想,像這樣系統地提出實行民主共和國的具體方案,鄒容也是第一人。
在鄒容心目中,法國革命和美國獨立是革命的最高榜樣。在他所提出的民主共和國的具體方案中明確地規定:「立憲法,悉照美國憲法,參照中國性質立定。」他特別推重法國革命時期的啟蒙思想家盧梭的
《約論》。在他看來,法國革命也好,美國獨立也好,都是盧梭等人的學說結出的豐碩果實。他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地寫到:
「夫盧梭等學說,諸大哲之微言大義,為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魂還魂之寶方。金丹換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於是。我祖國今日病矣,死矣,豈不欲食靈藥投寶方而生乎?則吾請執盧梭大哲之寶幡以招展於我神州之土。不寧惟是,而況又有大兒華盛頓於前,小兒拿破倫於後,為吾同胞革命獨立之表木。」
「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與今世界列強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聞文明之政體、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盧梭《民約論》、孟得斯鳩《萬法精理》、
彌勒約翰《自由之理》、《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檄文》等書譯而讀之也。是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鄒容《革命軍》一書的發表,在當時思想界,有如響起了一聲震撼大地的春雷。還由於這本書充滿著熾烈的革命熱情,筆調又通俗明快、犀利有力,使人讀著它就像觸到了電流一樣,無法平靜下來,這就更增強了它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書出版後不久,章行嚴在六月九日的《蘇報》上發表了《讀革命軍》一文。指出:「卓哉,鄒氏之《革命軍》也!以國民主義為幹,以仇滿為用,撏櫡往事,積極公理,驅以犀利之筆,達以淺直之詞,雖頑懦之夫,目睹其字,耳聞其語,則罔不面赤耳熱,心跳肺張,作拔劍砍地、奮身入海之狀。嗚呼!此誠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也。李商隱於韓碑『願書萬本誦萬遍』,吾於此書也云。」它出版後,翻印流傳極廣,風行海內外。香港翻印的稱《革命先鋒》,新加坡翻印的稱《圖存篇》,上海翻印的,有的稱《救世真言》,在橫濱與章太炎《駁康有為書》並列,稱為《章鄒合刊》,還有將它與《揚州十日記》合刊的,銷售總數當逾一百萬冊以上,在清末革命書刊的銷數中居第一位。
當時正在日本留學的魯迅曾說:「……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更有赴日留學生感慨地說道:「……我們在去日本的途中,就已經呼吸到了革命的空氣;到日本以後,又受到了更多的革命思想的影響,而且還參加了拒俄學生運動;這樣,改良主義思想在我頭腦中就逐漸喪失了地位……甚至在思想上便完全和改良主義決裂了。」
 如果說,鄒容的《革命軍》是從正面闡述了革命的正義性和必要性,那麼,章太炎的《駁康有為書》則是從批判改良主義反動理論的論戰中,論述了革命的巨大意義。這篇文章,是革命派對改良派正面進行批判中,第一篇思想性和戰鬥性都比較強的文章;也是在當時產生了巨大革命影響的一篇文章。 如果說,鄒容的《革命軍》是從正面闡述了革命的正義性和必要性,那麼,章太炎的《駁康有為書》則是從批判改良主義反動理論的論戰中,論述了革命的巨大意義。這篇文章,是革命派對改良派正面進行批判中,第一篇思想性和戰鬥性都比較強的文章;也是在當時產生了巨大革命影響的一篇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改良派散佈了一系列的謬論,來反對革命,阻撓人們走上革命道路。這些謬論中許多又同社會上長期存留下來的舊傳統觀念結合在一起,保持著巨大的影響。不堅決批判改良派的謬論,革命高潮的到來是不可能的。對此,章太炎逐一進行了痛快淋漓的批駁,提出了不少精闢的見解,這就幫助許多人從改良派的精神枷鎖下解脫出來,很有些所向披靡的氣概。
改良派企圖用革命將招致流血犧牲,來嚇唬人們不要參加革命。章太炎卻從歷史上論證:在專制政體下,人民要取得政治上的權利,流血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既知英、奧、德、意諸國數經民變,始得自由議政之權。民變者,其徒以口舌變乎?抑將以長戟勁弩飛丸發※變也。近觀日本立憲之始,雖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師在其前矣。使前日無此血戰,則後之立憲亦不能成。故知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為立憲所無可倖免也。」
改良派以人民智力道德低下、不配革命為藉口,來反對革命。章太炎則用具體的歷史事實論證:正是革命實踐,才是提高人民覺悟的最有效的途徑。
「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後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且勿舉華拿二聖,而舉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於饑寒,揭竿而起,固無革命觀念,尚無今日廣西會黨之儕也。然自聲勢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賑饑濟困之事業。豈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競爭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雖然,在李自成之世,則賑饑濟困不可已,則合眾共和為不可已。是故以賑饑濟困結人心者,事成之後或為梟雄。以合眾共和結人心者,事成之後必為民主。民主之興,實由時事迫之,而亦由競爭以生此智慧者也。」
改良派以革命會引起社會紊亂為藉口,來反對革命。章太炎則指出:革命不祇是破壞,同時也是建設:「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
改良派將光緒皇帝說成堯舜以來未有的「聖明之主」,要人們將一切希望寄託在他的身上。章太炎則竭力揭破這種偽造的神話,打倒這尊虛設的偶像。過去,在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下,皇帝的名字儼然神聖不可侵犯,天下臣民是萬萬說不得的。誰膽敢提一下,就要大禍臨頭,腦袋就要搬家。章太炎偏偏選准這個目標,直斥光緒的名字。一聲「載湉小丑」,震動遠近。頑固派為此暴跳如雷,中間派為之目瞪口呆,而革命派卻為之揚眉吐氣。它在當時所起的那種震動人心的思想解放作用,今天我們已不容易完全體會到了。
對康有為,章太炎更作了尖銳的揭露,指出他那封信名義上寫給南北美洲諸華商「要改良不要革命的信」,其實是寫給清朝政府看的:「宣佈是書,其志豈果在保皇立憲耶?亦使滿人聞之,而曰長素(即康有為)固忠貞不貳、竭力致死,以保我滿洲者,而向之所傳,借遵皇權保中國不保大清諸語,是皆人之所以誣長素者,而非長素固有是言也。榮祿既死,那拉亦髦,載湉春秋方壯,他日復辟,必有其期。而滿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勢力權籍,或不如榮祿諸奸。則工部主事,可以起複,雖內閣軍機之位,亦可以覬覦矣。」這確是一針見血之論。
 自章太炎《駁康有為書》發表後,傳佈內外,改良派在愛國群眾中的影響大大消弱。這篇作品,在革命派同改良派的理論鬥爭中,不愧是一篇起了巨大影響的光輝作品。 自章太炎《駁康有為書》發表後,傳佈內外,改良派在愛國群眾中的影響大大消弱。這篇作品,在革命派同改良派的理論鬥爭中,不愧是一篇起了巨大影響的光輝作品。
但是,《革命軍》也好,《駁康有為書》也好,最初還祇是秘密的出版物,傳佈和影響的範圍不能不因之受到很大的限制。當章行嚴為鄒容《革命軍》題簽時,「容曰:『此秘密小冊子,力終捍格難達。革命非公開昌言不為功,將何處得有形勢已成之言論機關,供吾徒恣意揮發為哉?』言下唏噓不置。」在這種情況下,經過他們的積極活動,《蘇報》終於成了他們公開進行革命宣傳的重要陣地。
《蘇報》,本在一八九六年創刊於上海公共租界內。創辦人是胡璋(鐵梅),但由其妻日人生駒出面向日本駐滬總領事館註冊。主筆最初是鄒弢。報紙內容多載市井瑣事和作奸犯科的社會新聞,文字粗陋猥褻,曾因刊登黃色新聞並有欺詐勒索等事被人控告。一八九八年,《蘇報》為陳範(夢坡)購得。陳原為江西鉛縣知縣,因教案落職,憤而辦報,力倡變法。以後,他的女兒陳擷芬又主辦《女學報》。一九零二年冬,南洋公學學生退學風潮發生後,東南各校學生運動風起雲湧。《蘇報》在這種風氣影響下,「增入『學界風潮』一門,乃大為閱者之所注目矣。」
愛國學社成立後,由於「倉猝成立,經費不足,因與《蘇報》約,每日由學社教員七人輪流擔任撰述論說一篇,而《蘇報》館則月贈愛國學社百金。於是,互受其利,而《蘇報》遂為愛國學社師生發表言論之園地」。一九零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蘇報》正式聘請愛國學社章行嚴為主筆。六月一日,是日蘇報大改良,於發論精當時議絕要之處,夾用二樣字體,錯落出之。是日之論說為《康有為》,其中「『革命之宣告,殆已為全國之所公認,如鐵案之不可移』數語,即政府所指控者也。」六月六日,「是日之論說為《祝北京大學堂學生》,以風聞北京大學堂學生接應東京義勇隊者二人被拘,且訛傳正法矣。其實並無此事,不過大學堂學生曾上書管學,請力阻俄約耳。而海上風謠四起,一日數驚。故《蘇報》有是論。大約此簦議論,乃《蘇報》中之最激烈者矣。」七日、八日,《蘇報》連續刊載論說《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九日起又連續刊載文章公開向讀者介紹鄒容的《革命軍》,發表大量鼓吹革命的文章。就在這時,《中外日報》發表了《革命駁議》一文,《蘇報》在十二日和十三日又連載了章太炎、柳亞子、蔡治民、鄒容四人合寫的《駁革命駁議》。言詞激烈,一切在所不顧。它猶如狂飆卷地襲來,上海新聞界原來沈寂的空氣頓時被一掃而空。
這個時期的《蘇報》,公然地、毫無顧忌地昌言革命。《康有為》一文中,除指出「革命之宣告殆已為全國之所公認,如鐵案之不可移」外,還寫到:「而天下大勢之所趨,其必經過一躺之革命,殆為中國前途萬無可逃之例。」《祝北京大學堂學生》一文用歐洲共和革命時期學生們起來「殺皇帝」、「倒政府」的歷史先例,來鼓舞人們大膽地行動起來,寫到:「學生為革命之原動力,而京都之學生為中央革命之原動力,是世界所供認者也。巴黎之學生、維也納之學生、柏林之學生、聖彼得堡之學生,撞自由鍾矣,樹獨立旗矣,殺皇帝矣,倒政府矣。」「北京學生諸君將追其跡,而照耀於二十世紀之歷史乎?將為先人雪恥,而壯大吾漢人之聲色乎?吾歌之,吾誦之,吾全國之學生將歡迎諸君矣。望諸君自重,諸君膽壯,那拉氏不足畏,滿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嚇而斂其動,莫惜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國人之希望。則學生之全體幸甚,中國幸甚。」「中國萬歲!中央革命萬歲!」
其中,寫得更激烈的,是《殺人主義》一文。這篇論說中,雖然表現了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但它所表現的那種同帝國主義的走狗清朝勢不兩立、鼓吹革命一往無前的精神,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寫到:「此仇敵也,以五百萬么魔小丑,盤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稅,殺戮我祖宗,殄滅我同胞,蹂躪我文化,束縛我自由。既丁末運,沐猴而冠,己不能守,又複將我兄弟親戚之身家、性命、財產,雙手奉獻於碧眼紫髯下。奴顏向外,鬼臉向內。嗚呼!借花獻佛,一身媚骨是天成;斬草除根,四海人心應不死!今日殺人主義,即復仇主義也,公等其念之。」他還寫到:「讀法蘭西革命史,見夫殺氣騰天,悲聲匝地,霜寒月白,雞犬夜驚。懸想當日獨夫民賊之末路,英雄志士之手段,未嘗不豪興勃發,不可複遏!黃旗已招展矣。借君頸血,購我文明,不斬樓蘭死不休。壯哉殺人!」
 《蘇報》對改良派散佈的教育救國論、變法維新論等阻撓革命的種種謬論,一一進行了批駁。對教育救國論,他們一針見血地指出:「奴隸主義者,以其知識技能盡奴隸之職。國民主義者,以其知識技能盡國民之職。夫以奴隸主義之人,而增其知識,練其技能,則適足以保守其奴隸之範圍,完全其奴隸之伎倆,將使奴隸根性永不可拔。是其非教育界之罪人、而我國民之公敵哉!居今日我國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導之脫奴隸就國民。脫奴隸就國民如何?曰:革命!」對變法維新論,他們嘲笑道:「夫大小變法,不過欺飾觀聽,而無救於中國之亡。」「總之,國民與政府,立於對峙之地者也。革命之權,革命操之,欲革命則競革命。維新之權,非國民操之,不操之權,而強聒於政府,亦終難躐此革命之一大階級也。悲夫,放棄國民之天職,而率其四萬萬神明之同胞,以仰一異種胡兒之鼻息,是又昌言維新者所挾以自豪乎?無量頭顱無量血,既造成我新中國前途之資料。畏聞革命者,請先飲汝以一卮血酒,以壯君之膽,毋再饒舌,徒亂乃公意。」這些對改良派的批判,比留日學生刊物如《國民報》等,顯得更旗幟鮮明、痛快淋漓,達到了當時最高的思想水平。 《蘇報》對改良派散佈的教育救國論、變法維新論等阻撓革命的種種謬論,一一進行了批駁。對教育救國論,他們一針見血地指出:「奴隸主義者,以其知識技能盡奴隸之職。國民主義者,以其知識技能盡國民之職。夫以奴隸主義之人,而增其知識,練其技能,則適足以保守其奴隸之範圍,完全其奴隸之伎倆,將使奴隸根性永不可拔。是其非教育界之罪人、而我國民之公敵哉!居今日我國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導之脫奴隸就國民。脫奴隸就國民如何?曰:革命!」對變法維新論,他們嘲笑道:「夫大小變法,不過欺飾觀聽,而無救於中國之亡。」「總之,國民與政府,立於對峙之地者也。革命之權,革命操之,欲革命則競革命。維新之權,非國民操之,不操之權,而強聒於政府,亦終難躐此革命之一大階級也。悲夫,放棄國民之天職,而率其四萬萬神明之同胞,以仰一異種胡兒之鼻息,是又昌言維新者所挾以自豪乎?無量頭顱無量血,既造成我新中國前途之資料。畏聞革命者,請先飲汝以一卮血酒,以壯君之膽,毋再饒舌,徒亂乃公意。」這些對改良派的批判,比留日學生刊物如《國民報》等,顯得更旗幟鮮明、痛快淋漓,達到了當時最高的思想水平。
《蘇報》的不少論說發表以後,外地報刊如香港《中國日報》、廈門《鷺江報》等紛紛選錄轉載,從而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
上海地區的革命宣傳活動如此大張旗鼓地迅速展開,自然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極大震動。這年的五、六月間,清朝商呂海寰就函告江蘇巡撫恩壽說:「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眾議事,名為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請即將為首之人密拿嚴辦。」恩壽就飭上海道袁樹勳向各國領事照會,指名要逮捕蔡元培、章太炎、陳範等人。介紹《革命軍》的文章在《蘇報》上發表後,恩壽再次飭袁樹勳,稱奉清廷諭旨,要求上海的帝國主義租界當局――工部局,會同查封《蘇報》,逮捕章、鄒、陳等人。又派候補道俞明震到上海,會同袁樹勳辦理此事。
六月二十九日,工部局派中西警探到《蘇報》館,捕去報社帳房程吉甫。第二天,到愛國學社逮捕章太炎。章太炎在被捕時說:「餘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同天,又在《女學報》館捕去《蘇報》辦事員錢寶仁和陳範的兒子陳仲彝。另有龍澤厚,也因自力軍舊案而被指捕,於當晚自動投案。鄒容最初由張繼藏在虹口一個教士家中,後亦於七月一日到租界巡捕房自動投案。
章太炎被捕後,在獄中致書《新聞報》記者,稱:「今日獄事起於滿洲政府,以滿洲政府與四萬萬人構此大訟,江督關道則滿洲政府之代表,吾輩數人則漢種四萬萬人之代表。」這封信在七月六日的《蘇報》上刊出。第二日,《蘇報》就被封閉。
七月十五日,英租界會審公廨組織額外公堂進行審訊。清朝政府委託律師古柏提出控訴,指責《蘇報》「挑詆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國民仇視今上,痛恨政府,心懷叵測,謀為不軌」云云。章太炎在受審訊時,慷慨陳詞,繼續宣傳革命,說:「因見康有為著書反對革命,袒護滿人,故我作書駁之。所指書中『載湉小丑』四字觸犯清帝聖諱一語,我祇知清帝乃滿人,不知所謂聖諱。」這次訴訟,引起國內輿論的沸騰,成為全國視線集注的焦點。案中的陳中彝、錢寶仁、程吉甫三人,因無關重要,被關押四個月後即被釋放。章太炎、鄒容二人,清朝政府原來堅持要求引渡到南京,準備置於死地。但在廣大群眾的強烈反對下,拖延到第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租界當局最後祇能判章太炎監禁三年、鄒容監禁二年。可是,鄒容在監禁期滿前兩個多月,竟「因病」死於獄中。「鄒容病急時,已許某時某日出獄矣。先一夕服醫生藥,遂死。故外間生疑,多謂遇毒。」章太炎被關押至一九零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方才出獄。
《蘇報》案的發生,對國內思想界的震動是十分巨大的。這件事在上海發生。它對內地所起的打開風氣的作用,自然是日本和香港等地所難比擬的。章行嚴在回憶中說:
「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言詞之間,略無忌諱,斥載湉為小丑,比親貴於賊徒者,維香港東京之刊物能為之,在內地則不敢,抑亦不肯。洵入上者,詞鋒朝發,緹騎夕至,行見朋徒駭散,機關搗毀,所期者必不達,而目前動亂之局亦難於收攝也。此其機緘啟閉,當時明智之士固熟思而審處之。然若言論長此奄奄無生氣,將見人心無從振發,凡一運動之所謂高潮無從企及。於是少數激烈奮迅者流,審時度勢,謀定後動,往往不惜以身家性命與其所得發蹤指示之傳達機構,並為爆炸性之一擊,期於挽狂瀾而東之,合心力於一響,從而收得風起雲湧之效。《蘇報》案之所由出現,正此物此志也。」
愚蠢的清朝政府,本以為借《蘇報》案就可以將當時方興未艾的革命思潮撲滅下去。但是,歷史的發展總是大出反動統治者的意料之外。《蘇報》案發生後,在國內知識界引起了更大的激動,更有力地促進了革命思潮在國內的廣泛傳佈。《蘇報》第四期的本省時評說得很清楚:
「前日之《蘇報》與《革命軍》,議論雖激,然而閱此報與此書者幾何人也?一般之國民固未嘗知其所號呼者為何事,其鼓吹者為何事。今日《蘇報》之被禁,章、鄒之被錮,其勢固已激蕩於天下。然『《蘇報》何以被禁,章、鄒何以被錮』之一問題,出諸於一般國民者必多,則必應之曰:為逐滿故。何為而逐滿?則又必應之曰:為漢族受滿族之荼毒已不勝其苦,滿族實漢族之世仇敵。以此而互相問答,互相傳說,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萬。於是,排滿之主義,遂深入於四萬萬國民之腦髓中。」
他們還特地發表《祝蘇報館之封禁》的時評說:「此後,吾但祝滿政府多封報館;則國民之自由心愈發達,吾中國前途愈光明。吾乃於《蘇報》館之事,饗宴以賀之,燃開花炮以祝之。」另一篇時評中更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後之革命風潮,當為奔濤怒浪,不可遏止。吾不知官吏政府,又將以何術濟其窮?」
《蘇報》案尚未結束,在北京又發生了清朝政府杖斃參加自立軍的沈藎事件。沈藎,原名克誠,字愚溪,湖南長沙人。先時,與譚嗣同、唐才常友善。他在維新派中是思想比較激進的一個,曾說:「新吾湖南,非有一番之破壞,不為功也。」戊戌變法失敗後,曾東渡日本。後回上海,參與唐才常主持的自立軍事件,為右軍統領。但,「藎所恃之主義,乃唯一之破壞主義,不喜學問,無複雜之頭腦,故一聞才常之言,以為天下事大可為也。」事敗後,潛入北京,秘密居住兩年,被人告發。一九零三年五月十九日,被清政府逮捕。這時正在《蘇報》案事件起後二十天。沈藎被捕後,被判死刑。這時,正值西太后生辰,嫌在這時行刑會「破其慶典」,於是就下令在獄中杖斃。七月三十一日,清吏用竹鞭捶擊沈藎,連續四小時,血肉橫飛,乃未絕命,最後用繩子勒斃。
這個事件,充分暴露了清朝政府的野蠻殘暴,激起了人們的極大憤怒。《江蘇》雜誌的國內時評寫道:「夫沈藎以何罪死,滿政府固未嘗有一紙死罪宣判書以告我國民也。夫殺而不能言其罪,則四萬萬人孰非可殺之人乎?」,「嗚呼!吾向者猶以為滿政府不過用其呼爾蹴爾之術以待我漢族,而不知今後竟至於磨刀霍霍而來也。今日杖殺一沈藎,不過小試其新硎之利器耳。血肉橫飛,哀呼宛轉於槌杖之下,又滿政府待我漢族之方法,而我同胞前途之寫影也,吾同胞其將何以待之?」章行嚴更於同年化名「黃中黃」寫了《沈藎》的小冊子(章太炎在獄中為這本書作了序),書中指出:
「自藎死後,而滿政府之醜狀盡形呈露,大激動國民之腦筋,發議於各新聞雜誌,以為今日可以無故而殺一沈藎,則明日即可以無故盡殺吾四萬萬同胞。前言滿族之虐待我漢族,而尚有忠奴為之解脫,自今觀之為何故?同胞視此,則直以為滿政府與吾國民宣戰之端,吾國民當更有一番嚴酷之法對待滿政府。幾致全國之輿論為之一轉。」
上海的激進份子又在愚園召開隆重的追悼會,到會的有數百人。會上,宣讀章太炎所撰的哀詞,鞠躬致敬,並有人演說沈藎慘死的事實和今後對待清政府應有的態度。到會的人中間,不少人為之流淚。
這樣,從《蘇報》案以後,革命思潮在國內,也如決堤的洪水一樣,衝破種種傳統思想的嚴重束縛,洶湧澎湃,一發不可收拾地向前推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