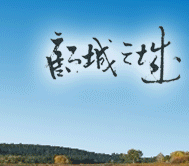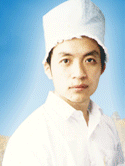在地铁书摊见到《北岛诗歌集》时,我惊讶已极。想不到竟会与这位销声匿迹多年的诗人在此相逢——诗集周围层层叠叠着小资中产白领读本,诗集的装帧本身也在尽可能的素朴之中透着纤柔的样貌。它呆在那儿,似乎宠辱不惊,似乎等着一位记忆复苏的知音,似乎暗示着平静的能力和勇气,就这样北岛重又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我是在地铁的轰鸣声里断续读完了这本诗集的——据说它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岛在内地印行的第一部诗集。地铁这个地方几乎帮我建立了判断诗好诗坏的标准:好的诗总能把我带进暗流汹涌的寂静中,而忘掉身边嘈杂的人群;不好的则相反——觉得地铁吵,诗更吵,情绪会因此变糟。在地铁里读北岛的时候,心情不糟,但是复杂,蜿蜒的铁轨无端地沉重,似是一条时光隧道,带我跨越30年的时空。
是30年的时空。不明白诗集为何抹去了每首诗的写作时间,这是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好在我能够大体知道,它收入了北岛从1972年到1998年间的重要诗作。现在读这本诗集,使我突然清晰地意识到,北岛那些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震撼了他的同代人的诗,经由他们的传递,也早已在我这个“70后”心里烙下了深刻的印痕,尽管我对它们的初次阅读,要等到好几年之后的80年代末。在沉默的抽象生涯里,我们这些一无所历一无所见的“70后”也照样能感到《回答》、《太阳城札记》、《一切》、《宣告》、《结局或开始》的能指与所指。我们也照样能听到其间血液的呼啸。我们也照样能体会它们所言说的热和冷,绳索与自由,爱情与正义,死亡与真理。是的,我们照样能读懂北岛,欣赏北岛——以审美与传说的方式。这是“70后”一代的宿命:我们依稀的童年和青春记忆与北岛一代接壤,但是这种蒙童般的旁观经验却很难形成清晰的意识和有形的言语;它们涌动在我们的生命内部,虽无法发声,难以命名,却成全了一种跨时代的理解力。因此,北岛从经验中诞生的早期诗歌,到我们这里则需靠对记忆的参与性想象来达成对它们的理解(并不费力地)。我们自认为能够理解,因这些诗本身清楚易懂,刀锋向外;我们曾痴迷和感喟,为这些诗的血性的质地和铿锵的韵律。但同时,我也知道北岛的语言不属于我们——历史的亲历者和旁观者、先到者与迟来者永远不可能使用同样的语言。我这个“70后”,对早期的北岛抱有无限的怀念和无尽的诘问,而怀念和诘问的理由却无不堕入经验的虚无中。我不知道,晚生于我的“80后”、“90后”们,乃至之后的无穷世代,对北岛的早期诗歌会有何种认知。
也许北岛对此早有意识,因此他对自己的早期作品批判得比所有人都严厉。在一篇访谈里,他说:“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
北岛90年代以后的诗,的确与早期有极大的不同。技艺更圆熟。声音更内敛。是他独自的低语。有时似自己对镜交谈。寂静与孤独时而对他构成威胁和敌意,时而引起他对往昔自我的反讽与自省。这些诗有着佯装的平静和易碎的紧张,随时准备像火山爆发。时有妄念。幻觉焦躁。前生的光荣似一直如影随形,干扰着诗人蝉蜕和新生的自我。竭力谛听此岸自我的真实的声响,竭力与昔日的荣耀和惯性的渴求作斗争,竭力沉入现在之中,是这些诗传递给我的朦胧而晦涩的信息。90年代以后的北岛不再易懂,在多年的海外漂泊中,在对母语环境的疏离与反观中,北岛变成了一个更为内在的诗人。他不再是伤痕累累的雕像般的“我们”,他只成为了他自己。
但是,如果没有《回答》,没有《一切》,没有《宣告》,没有《结局或开始》,北岛还是北岛吗?即使他现在写了无数更娴熟更完美的《第五街》?无论如何,在喑哑的年代里,那根最深沉的喉管里爆发出的最疼痛的声音,是永远最值得人们追忆和感念的。我们这些后来者,需对此致敬。